索尼娅:《变形》这个标题唤起了一种持续的转变。您能否谈谈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答: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视野中,世界的变化的形态也许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周围的事物发生的变化极其敏感,也有人视而不见。世界的变化,其实也是人的变化,人的观念的变化,人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判断、对未来的憧憬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变化。我的很多诗作,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描述,也许非常主观,是一孔之见,是有别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觉,但对描述者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恒定不变的事物,但这些不变,大多是精神的产物,譬如心中的某些执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不管周围的现实如何喧嚣,保持心绪的宁静,坚守自己的目标,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虚伪,不媚俗。我曾经用“礁石”作为自己在网上的笔名,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经受汹涌的海浪永无休止的冲击,但他永远以不变的姿态屹立着。但浪中的礁石其实也在变,海浪的冲击和腐蚀,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迹,那是在远处无法看清的累累伤痕。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索尼娅:本诗集中许多诗歌探讨了记忆、时间和变形等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反映在您的个人生活体验中?
答:记忆这个词,涵盖了过往的所有时光和经历。不管是清晰的往事还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轰轰烈烈的事件还是幽光闪烁的瞬间,都是记忆。我的大多数诗作,都和记忆有关,在我的诗中,它们展现的也许是一段往事、一个人物、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一段音乐、一件器物、一丝微笑、一滴眼泪……在沉思时、在旅途中、在梦境里,它们无时无刻地会叩响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门,给我写诗的灵感。而所有这一切与记忆有关的诗句,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时间。时间笼罩着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也许还有另一个主题:变形。记忆中的景象,经过时间的酝酿,重现在诗句中时,已经面目全非。
索尼娅:在诗歌《此生》中,您讨论了痛苦与快乐、斗争与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这种二元性在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答:《此生》这首诗,其实是对人生的反思、对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诗作,都是在做这样的反思。回溯生命的过来之路,有迷惘忧伤,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悦,有欢乐的笑声。那些不同的情绪,在生命中不时交替,也经常是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状态中的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他们之间的冲突纠缠,无时无刻地陪伴着每一个人,让你沉迷,让你困惑,让你惊恐,让你忍不住回头寻找自己的脚印,也不断审视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时自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娅:在《平衡》这首诗中,您探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这种张力如何影响您的诗歌创作?
答:你把这首诗的题目翻译为《平衡》,中文原诗的题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种测试轻重平衡的仪器,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意象。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平衡。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只是一些我们希望抵达的瞬间。而不平衡,却是生活的常态。在诗中,我让自己站在一台天平仪的中心,试图以自己的移动来控制天平两边的平衡,而天平的两边,不是具体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两个无法触摸的抽象概念:过去和未来。使自己成为平衡支点的想法,当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样移动位置,也无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去和未来,每个瞬间都改变着它们的位置,时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运转也自有其规律,在失衡的天地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态度。正如孔子所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娅:您的诗歌《通感》在感官与感知之间进行了探讨。通感在您的创作过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答:通感是一种修辞手段。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以相悖的事物折射你想表达的意象。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相互沟通转换,由此及彼,不分界限。以《通感》为题写诗,是用这样的修辞手段,把人的情感、欲望和人生中种种迷惘、失落和希望,表达得曲折幽邃,让人感觉到一种神秘。而这样的神秘感,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地躲藏着,也无时无刻被遭遇着。直白地写出感受,也许平淡无奇,神秘感随之消失。如果借用通感的手段,非常规非常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给人更深刻的印象。通感的手段,其实经常出现在我的诗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光芒可以有声音,声音和气味可以变为具象的物体。譬如《温柔的暴行》,也是通篇都用了通感的手段。
索尼娅:《我的沉默》这首诗似乎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沉默对您作为诗人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答:沉默是什么?是无声,是哑口无言,是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和能力?一个思想者,一个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变成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声音,那意味着死亡。你说我的这首短短的诗“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谢谢你的理解!中国人有一句谚语:沉默是金。涵义其实很复杂,它的意思并非简单地赞美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高洁的智者。当人声喧嚷,人人都争着发声、争着表态、争着表现自己的聪明或高尚的时候,你的静默的姿态,你隐忍不发的态度,表达的是你的独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实有声音,这声音,也许振聋发聩。我的不少诗,其实是在沉默中写的,在赞美这种沉默的态度时,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但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索尼娅:《木偶》这首诗中的隐喻非常强烈。这一形象如何与您自身的生活与艺术中的自主感或控制感产生共鸣?
答:牵线木偶是中国福建省泉州地区的传统民间艺术,非常美妙。小小的木偶被一根根看不见的细线牵动着,在舞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的悲欢离合,被这些牵线木偶表演得栩栩如生。你看这些木偶活动时,会忘记他们是被人牵动的玩偶,仿佛是面对着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但是他们完成表演之后,身上的线松弛了,他们就变成了一堆布片,瘫倒在地上,被人扔进道具箱。活动的木偶,是被人操纵的,是傀儡,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是传达牵线人的意志。木偶的形象,确实是一种隐喻,人类历史中,过去的时代和我所经历的时代中,这样的形象并不少见。可悲的是,很多被人牵线操纵着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形同木偶。写这样的诗,不仅是一种哀叹,也是一种警醒。
索尼娅:在《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您借助哲学人物探讨了存在问题。您与哲学的关系如何?哲学又如何影响您的诗歌?
答:《在天堂门口》是这本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三百多行,集叙事、幻想、抒情和议论于一体。诗中出现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庄子、孔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们相聚在天堂门口,却无法进入。因为,天堂门口藏着无形的斯芬克斯,这一群伟大的哲人,都无法回答来自天堂门内的提问。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个寓言,也是我对人类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一种看法。我在诗中和每一位哲人对话,但都是浮光掠影,无法真正进入他们的思想之海,无法窥清他们的真实的灵魂。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们一生都在追寻的道路上,但没有一位能抵达终极的目标。他们的追寻和表达,营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哲学花园,引人入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幽深的花园里找到自己欣赏的花草,但没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称:我就是美的终极,我就是真理的尽头。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创造和表达,其实都处在一个寻求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以抵达终极之点。无数这样寻求的过程,汇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让芸芸众生在其中游览、观赏、沉思、感悟、惊叹。我想,哲学对我的诗歌的影响,在我的每一首诗中。而《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也许有集中的体现。这首长诗在中国的一家重要的文学月刊发表后,获得了这家刊物当年的诗歌大奖,我曾为这家刊物写过一段获奖感言,附录如下:
关于《在天堂门口》
三十多年前,我曾经以《在天堂门口》为题写过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和宗教无关,和哲学也没有关系,文中天堂的指代,是音乐。欣赏美妙的音乐,如同站在了天堂门口。在音乐厅里,专注的听众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状态,有张嘴惊愕,有闭目遐思,有微笑沉醉,也有人泪流满面。相同的音乐,却使聆听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表情,这是面对天堂的神态。我在文章中写了一位特殊的听众,外表粗陋,却深谙音乐内涵。一个人身上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至今仍不了解,是记忆中一个不解之谜。最近以相同的题目写的这首长诗,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和主题,但其中隐隐有些许联系。
今年病毒肆虐,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在失常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变化。人类不了解突然泛滥的病毒,在惊恐不安的同时,对很多传统的思维定义也产生怀疑。这个世界,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明天将会是什么模样?人类对真理的探求,数千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抵达终极。很多当代中国人以仰视的角度崇拜西方的哲学,认为人类最深刻的思想在那里,接近终极真理的思考也在那里,却无视更为阔远深邃的中国人的哲思。如果把人类追求的终极真理看作天堂之门,那么,这扇门到底在哪里?到底为谁而开?
长诗中的天堂之门,指代的是终极真理。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很多人自以为接近了这个天堂,甚至已经叩响天堂之门。然而,这扇门,被谁打开过?我想象着千百年来前赴后继奔向这扇门的哲人们,老子、庄子、墨子、孔子、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苏轼、王阳明、顾炎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笛卡尔、尼采、罗素……我想象着这些诞生于不同的时代,说着不同语言的哲人,都被挡在了这扇门外。这些伟大的名字和他们所承受的名声,甚至可以对这扇门不屑一顾,然而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历尽磨难,却找不到那把可以开门的钥匙。如果他们在这扇闭锁的大门口相遇,会出现怎样的情景?我想起了30多年前写的那篇散文,想起那些沉醉在音乐中千姿百态的表情,想起那位外表和内心显示极大反差的爱乐者。
我的诗,也许荒诞,但能在诗中和先哲邂逅,遐想人类遥无尽期的追寻之道,虽只是远观,只是神游,只是臆测,却也可以因此收获莫大的沉醉和快意。企图以诗歌解开天地之谜,提供准确答案,这是妄想。世间永不会出现天堂门口的景象,但文学可以自由想象,并引发思索。天地之间,有太多不解之谜,诗歌的迷人之处,也许正是在不断地提问中。
2020年11月18日于四步斋
索尼娅:在《母亲的书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亲。母亲这一形象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和诗歌道路?
答:我诗中写到母亲,这是生活中真实的感受。母亲爱我、关心我,我曾经认为母亲不会关注我的创作、不会读我写的书,因为她从不主动说。多年前,我发现,在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她自制的书架,书架上放的,都是我写的书。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书最完整的书架。对母亲的关爱,我无法用文字完整地表达我的感动。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母爱,我有这样的母亲,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岁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要第一个送给我的母亲。我不会在每一首诗中写到母亲,但母亲的关注和爱,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励,成为我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母亲的书架》是一首纪实的诗,这样的情景,人间稀罕,只需要用朴素的文字写出来,母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深情就饱含其中了。写这首诗时,我母亲98岁。2024年1月,103岁的母亲与世长辞,我想念她!我会为母亲写一本书,不是诗集,但书中一定有我和母亲共同完成的诗篇。
索尼娅:本诗集以非常哲学性和沉思性的基调结束。您如何看待您未来诗歌的演变?您希望通过写作探索哪些新的领域?
答:诗歌中有哲学、有思辨、有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和思考。但哲学家的结论,不应该出现在诗人的文字中。中国古代的诗人,也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中国的古诗,在唐代是一个高峰,唐诗的境界千姿百态,以风情神韵见长。到宋代,诗人追求以理入诗,曾被后人诟病。这样的争论,各执其词,其实并无胜者。诗歌和哲学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结合和关联,我在长诗《在天堂门口》有所表达,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见。未来的诗歌会有怎样的演变,我无法预言,我大概不会改弦更张,也不会标新立异,还会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
(2025年1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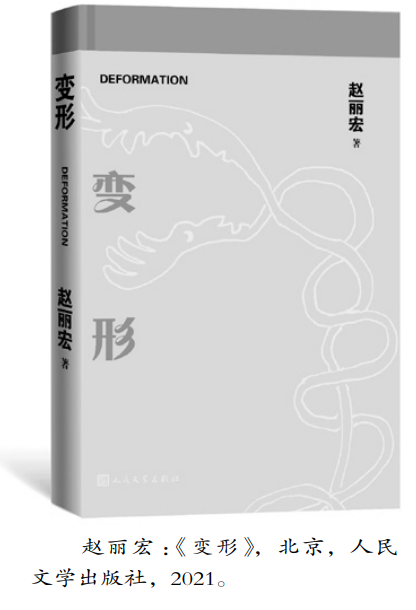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