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湖南醴陵这片热土,孕育了两位道路殊异却命运交织的人物——杨东莼与刘斐。他们从同窗少年到阵营分野,再到民族危亡时并肩作战,在近代中国的激荡浪潮中,共同书写了一段交织着理想与抉择的往事。
幼同里,长同校:革命意识的萌芽
1913年的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的院落里,一场震动地方的罢课学潮正悄然兴起。13名热血少年以“自由平等”为旗帜,持续75天的抗争席卷校园,李立三、李明灏等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名字赫然在列,杨东莼与刘斐便是其中的活跃身影。彼时的醴陵虽处内陆,却因湘军百年积淀的变革基因,弥漫着对旧秩序的质疑——这场学潮,恰似一粒火种,在两位少年心中播下了反抗与革新的种子,成为他们革命意识的最初启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两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分野。杨东莼北上求学,考入北京大学后沉浸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在李大钊等先驱影响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刘斐则循着湖湘子弟“投笔从戎”的传统,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后凭借过人军事天赋,逐渐成为桂系倚重的智囊。这一分叉,预示着他们将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呼唤。
东京偶遇:异国他乡的相知与相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杨东莼与刘斐竟不约而同辗转至日本。杨东莼因身份暴露前往东京,潜心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图“笔杆子救国”;刘斐则被桂系保送至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异国街头的偶遇,让这对同乡重逢于困顿与求索之中。
彼时杨东莼生活拮据,不仅要筹措学费,还需兼顾译著开支,刘斐当即让夫人腾出家中一间空房,邀他同住。杨东莼患病时,刘斐更是解囊相助,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两人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对彼此的认知:刘斐见证着这位北大才子的学术成长——抵日数年间,杨东莼译著颇丰,1929年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出版后,以精准的译笔和深刻的阐释震动国内学界;1931年,他撰写的《本国文化史大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以唯物史观重构中国文化史,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的必读书目。而杨东莼也愈发敬佩刘斐的军事才思与务实精神,常在交谈中感叹“同乡中藏此将才,国之幸也”。这次偶遇,为两人日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1932年,广西筹备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范大学前身),急需一位兼具新思想与学术声望的校长。刘斐向主持广西教育的李任仁力荐:“杨东莼乃北大高材生,不仅学问精深,更懂育人之道,此人掌舵,师专必成西南学界重镇。”在他的力促下,杨东莼出任该校首任校长,以“培养革命的师范生”为宗旨,并聘请夏征农、艾思奇等进步学者。该校成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共赴国难:殊途同归的爱国担当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曙光初现。杨东莼受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对新桂系开展统战工作,他第一时间联系刘斐:“国难当头,昔日分歧皆可暂搁,唯有团结御侮,方能救亡图存。”两人在南岳衡山彻夜长谈,随后一同赴桂林劝说桂系。最终,桂系公开表态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斐赴南京,向国民政府传递桂系立场,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添砖加瓦。
抗战胜利后,两人虽再度因政治立场分属不同阵营,却始终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刘斐曾坦言:“东莼兄的思想锐度与人格操守,即便意见相左,我亦由衷敬佩。”杨东莼也常对人说:“为章(刘斐字)的军事才能与爱国心,不容否定。”1949年,刘斐参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投向新中国,这一抉择的背后,或许正潜藏着早年与杨东莼交往中埋下的进步种子。
回望这段往事,杨东莼与刘斐的人生轨迹,恰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路径多元,爱国初心归一”的缩影。他们以同乡之谊在民族危亡之际坚守着共同的底线——这份家国情怀,至今仍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作者系民进株洲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2025年8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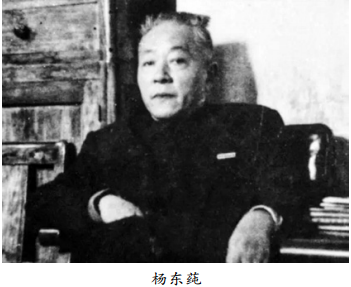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