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当代文学批评、散文创作。已出版《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文学理论十讲》《五种形象》《无名的能量》《文学的位置:挑战与博弈》等学术专著、论文集三十余部,出版《辛亥年的枪声》《村庄笔记》等散文集二十余部,两度摘得“鲁迅文学奖”,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朱自清散文奖“杰出作家奖”等多个奖项。
工夫在诗外
我曾经多次言及随笔写作带来的快乐——超过了论文写作。供职于专业研究机构,论文写作属于日常事务。我屡屡不务正业,抛开论文逛到随笔的领地。我时常盘算着一件事情,哪一天厌倦了理论的高头讲章,退出江湖,随笔大约是一个寄托心情的所在。长短不拘,随物赋形,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短笛无腔信口吹”,所思所感的自由表述不仅是为文之乐,也是为人之乐。
那一天早晨突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快乐?写作难道不是心力交瘁的煎熬吗?的确如此。为什么内心充满喜悦地自讨苦吃?精神分析学曾经抛出一个有趣的解答——那些作家之所以奋笔疾书,恰恰因为一个巨大的精神冲动。某种内心能量急不可耐地破门而出,疲惫、苦恼、强权的威胁,身体遭受摧残甚至命悬一线都无法扼杀写作的渴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解释“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事例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念,“郁结”的内在原因往往与严重缺失的经验密切相关。无论是父母庇荫的缺席还是强烈欲望的受挫,缺失作为精神创伤沉淀于无意识深部,不时渴求各种象征性的补偿,譬如孜孜矻矻的写作。作品构筑的另一个世界曲折地补偿缺失制造的遗憾;作家之所以下笔千言,毋宁说是用语言追逐、捕获、占有、填补那个缺失。概括地说,写作的快乐,即抚平缺失与挫折造就的精神落差。当然,所谓的缺失从未真正平复,而是周而复始,络绎不绝;因此,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精神动力一辈子不可能枯竭。现在,我终于将自己安置在这种理论故事之中充当主人公,分析执笔为文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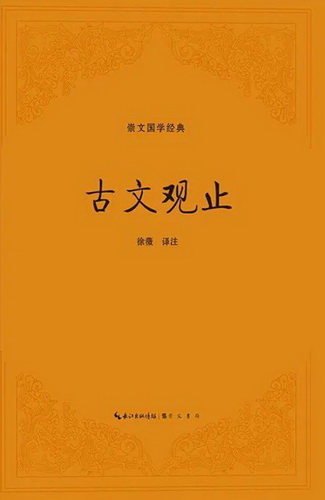
《古文观止》,崇文书局2023年版
论文写作的意义是证明或者反驳各种命题。众多命题或者来自学术范式的分配、学术逻辑的延伸,或者由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发展状况提出来。之所以交付论文予以阐述,因为这些命题并非社会公认的常识。许多时候,论文的使命包含扩充常识、说服常识乃至纠正常识。当人们认为这些命题可能抵达科学或者学术的前沿地带乃至填补空白的时候,社会文化的“理想高度”无形成为有待于充实的“缺失”。因此,论文写作积极回应各种思想挑战,论证、思辨、逻辑性阐述以及披荆斩棘获得的结论伴随强烈的成就感。一个形象的比拟是,论文写作提供的快乐如同对弈。
论文写作之余,之所以转身与随笔握手言欢,很大程度上因为剩余的思想边角料。这些边角料无法纳入规范的论文形式,不得不另谋出路。尺短寸长,许多边角料恰好填补论文无法覆盖的思想缝隙。无论言志还是载道,论文阐述的各种命题具有普遍意义,论证的结论必须抵达公众共同认可的思想高地;相对地说,随笔表述的思想与智慧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个人的独特发现甚至比公众的认可程度更为重要。论文的内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或者构成某个学科的组成部分;随笔往往穿透大概念、大事件而抵近日常生活乃至身体,流露出浓厚的烟火气息,譬如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七情六欲、飞短流长。论文不得不诉诸实验室数据、数学计算,引经据典或者有严密的逻辑推论,这种语言是由结论的公共性决定;随笔没有必要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是嬉笑怒骂、不拘一格,可以幽默、揶揄,可以讥讽、调侃,散淡逍遥,何必拘泥?
通常认为,论文是学术的存身之地。然而,所谓的学术,并不是隐藏于深奥词句背后的某种秘技,而是事实的发掘、整理、描述,义理的疏通、阐发、论证。除了堂而皇之的标准论文,是不是还存在众多的另类表述?一则寓言或许缺乏大前提、小前提、推理与结论的完整程序,但是,象征或者联想的话语结构具有一目了然之效。相对于形而上的思辨,随笔倾向于经验主义,并且尊重常识;相对于重重叠叠的概念考证与引文注释,随笔倾向于一针见血、涉笔成趣,相信世间的某些真理可以在打趣之中泄露出来。始于事实,明乎义理,随笔时常显示出大跨度的内在跳跃:吃红烧肉,读圣贤书,听小道消息,写大块文章,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说的是若干传闻轶事,演绎的是严肃的为人处世。我的心目中,“随笔”这个称谓隐含松弛解放之感,坦然率直而不是刻意矫饰,宁可乱头粗服,不可搔首弄姿;随笔接近品茗闲聊,而不是舞台上花枝招展的表演。
什么是“剩余的思想边角料”?这种表述至少证明某种视域或者选择机制的存在。二者决定各种事物的轻重缓急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位置。然而,视域或者选择机制的重大转换可能深刻调整意识屏幕结构,重新分配世界的显现秩序。笛子无非一种常见的乐器,烟斗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日常用具;然而,当一支笛子成为恋人的信物时,当一个烟斗是祖父遗留的纪念时,衡量与评判的尺度迥然不同。众生平等,万物齐一,每一种事物的重要程度源于人为地赋予,所谓的“边角料”可能在另一个时刻出其不意地成为众目睽睽的轴心。作为规范严密的文体,论文必须将各种事物纳入严谨的因果链条,层层叠叠铺设抵达结论的台阶;论文的视域时常由逻辑架构掌控,设计环环相扣的理论轨道。相对地说,随笔的思想线路短促清晰,同时形成网状的发散状态。因此,充当网结的各种事物往往显现出更多的独立性质,事物周边环绕、编织的微型感想如同一圈光晕,摆脱了论文思辨的强大吸附力,随笔的思想始终与日常生活声息相通。
聚焦于日常生活的时候,另一个不可回避的追问是——为什么钟情于随笔而没有拐向小说?无论是烟火气息还是微型感想,日常生活同样是小说的基本材料。然而,作为重组世界的一种话语方式,大多数小说力图构造连续性经验。这种连续性经验按照人物命运的中轴线渐次展开,从而形成起伏曲折的情节。相形之下,随笔不屑于将零散的经验连缀成一个整体。这并非因为随笔的篇幅限制,而是因为一种深刻的怀疑:当世界被串成一个彼此衔接的链条时,每一个片段隐含的多种可能是否遭到线性整体的无形压抑?随笔试图将这些片段截取出来,单独地观察、解剖可能释放压缩的种种内涵,从而显现世界的另一种面目。小说的文学声望首屈一指,但是,随笔的意义之一恰恰是阻断连续性经验——避免小说的巨大声望封闭另一些认知世界的形式。
虚构与否同时显示出小说与随笔的分歧。对于成熟的小说而言,“虚构”并非纪实之余无奈的叙事补充,而是意味深长的精神扩充。按照精神分析学观念,为什么“虚构”以及“虚构”什么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消遣,而是再造生活之中匮乏的内容。如同一种“白日梦”,“虚构”不仅表明情节的虚拟性质,而且,这些情节同时寄存了人们的渴望、向往乃至信念和理想。许多时候,小说写作犹如再度创世,以想象的形式为自己提供诗意的栖居之所。但是,“虚构”显然倾心于传奇性。对于多数人来说,日常的平庸几乎是无法抛开的枷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不得不身陷无数琐碎的事务,重复枯燥乏味的日子。无论是古代的笔记小说还是说书话本,传奇性是人们挣脱日常生活的出口。现代小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形式转换,传奇性仍然充当显赫的叙事传统。作为一种文学特权,“虚构”不制造传奇还制造什么?纵横江湖,快意恩仇;倾城美人,终成眷属;吉人天相,挥金如土;才高八斗,万众瞩目……这些八辈子遇不到的好事,小说之中一应俱全。然而,随笔并未遭受传奇性的绑架。看穿跌宕起伏制造的情节幻影,气定神闲,不为所动,种种炫人耳目的良辰美景不是终将返回通常的人情世故吗?随笔宁可闲坐于树荫之中,等待那些撤出传奇的疲惫读者。油腻的盛宴之后,一杯苦茶才能清心明目。在我看来,随笔恰恰因为洞悉平淡包含的趣味而不屑于虚构。谁说只有传奇性才能打发无聊的日子?置身于日常生活,随笔找得到足以与传奇性相互抗衡的内容——没有必要虚构那些旷世的阴谋、动人心魄的爱情或者与外星人大战三百回合,日常生活带动的种种奇思妙想绝不亚于传奇性制造的悬念。
日常生活是辽阔的沃土。然而,随笔并非慵懒的闲逛,而是一种耕耘——期待思想的种子破土而出。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蒙田的散文随笔具有后现代性质。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主义的愤世嫉俗显现出不合作的抗拒姿态;不合作意味着超越,也意味着“深度”——突破日常生活表象的形而上之思或者拒绝世俗的另类立场。后现代开始放弃各种“深度”而将历史展示为一张平面。滑行于历史的表层而不再相信世界背后还存在什么,后现代显示出一种无所作为的轻松与游戏精神。蒙田的散文随笔轻盈地掠过日常生活的众多小题目,随心所欲地发表各种睿智的感想。他不是聚精会神地搜索什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构建某种宏伟的思想大厦,而是东鳞西爪,零散破碎,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后现代不再沿袭现代主义的倨傲从而与日常生活达成和解。但是,外部世界与主体之间的落差可能完全消失吗?在我看来,二者的张力始终存在,只不过显现为另一些形态。事实上,亲密无间地融入日常生活将丧失任何写作动机。因此,尽管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深度”不再构成一个异于日常生活的整体,但是,他所聚焦的一个又一个小题目仍然刺破了日常生活的光滑表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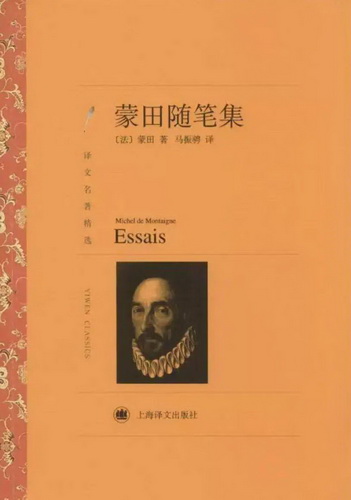
《蒙田随笔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鲁迅或许是人们熟悉的另一个例子。鲁迅杂文随笔涉及的范围超出了蒙田,他也不屑于将众多的感想装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许多时候,“整体”或者“体系”如同形而上学或者历史总体论带来的一种执念,仿佛一个完整的精神宫殿可以抵御历史洪流的侵蚀。浩渺的宇宙之间,哪一种“整体”或者“体系”不是碎片?事实上,碎片并非缺乏“深度”。鲁迅对于杂文随笔的自我期许是“匕首”“投枪”,两种锋利的武器深深地穿透了日常生活。一些教授曾经费心论证,鲁迅的庞杂作品背后存在一个“隐蔽”的体系。对于多数人来说,鲁迅介入日常生活的程度肯定比是否完成体系更为重要。
我当然还要提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大约三十年前,我偶尔读到巴特的《艾菲尔铁塔》与《神话集》,立即惊为天人。与鲁迅的激愤不同,巴特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深邃而精妙。巴特喜好短句、短的段落,两三页纸的短文很多,文辞机敏而坚硬。巴特同时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与符号学家,曾经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领域充当骁勇的先锋,但是,雄厚的理论基础并未磨钝他的感觉。巴特仿佛信手抓住日常生活的各种片段,破译凝结其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密码。这是他的一个尖锐发现:许多貌似“自然”的现象乃是某种文化合成物。这些文化合成物的拆解可以暴露与敞开许多人工设计的内在机制,促使人们追问这种设计是否合理。因此,拆解即是对盲从的抵制与批判。巴特的观点对“文化研究”的学术潮流产生了重大启示,以至于他被奉为“文化研究”的鼻祖之一。巴特的《神话集》可以视为这种观点的精彩实践。处理日常生活的众多素材,巴特的犀利分析并未脱离大众的接受范围——《神话集》的那一批短文是巴特写给报纸的专栏文章。
所谓的日常生活,并非一个天经地义的构造。一砖一瓦,一饮一啄,晨钟暮鼓,车水马龙,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一切理所当然。人们似乎可以目不斜视地穿过红尘滚滚的俗世,遥望天际的宏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理想的境地。然而,这个大叙事并非从天而降的固定理念,而是各种小叙事精心组织起来的。从饮食装束、一颦一笑到待人接物、世情冷暖,从父严母慈、男欢女爱到吃苦耐劳、从善如流,无数规范渗透现实的每一个细节,使之成为无可置疑的“自然”。这种“自然”由众多文化意象组成:从林林总总的器物到语言现象、规章制度。这些文化意象通常存在表象与内涵两个层面,如同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一座宫殿不仅是居住之所,同时还象征威严与宏伟;一束梅花不仅是普通的植物,同时还表示孤傲与高洁。解码这些文化意象的内涵,亦即解码各种文化叙事的内在构造,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文明七巧板》的写作初衷。《文明七巧板》收集了一批日常生活触目可见的文化意象并给予分析,譬如面容、镜子、家具、证件、化妆、服装,或者姓名、谣言、誓言、争吵、名声、电视,如此等等。我在“后记”之中分析了“分析”的意义:
我的分析游戏导源于凝视。凝视是一种简单的活动。可以端坐于居室内部的一把椅子上,也可以伫立于闹市街头,专心致志地注视某一个对象,这就是凝视。凝视在于用眼光切割对象,使之剥离日常的实用关系网络,进入特定的分析试管。这时,对象深部所寓含的曲折涵义就会慢慢地浮现出来——这种状况令人联想到印相纸沉浸于显影液之中所发生的奇妙变化。
人们经常轻易地接受环绕于周围的一切。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正前所未有地主宰人们的精神。接受是一种被动的姿态,接受意味着不加反抗地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分析以暂时退出环境来恢复人的主动。分析必须同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抗拒对象的动人的迷惑,从而在拆解对象的同时重新上升为对象的主人。分析是精神的反征服。
必须承认,日常生活内部涌动着强大的惰性。作为一种轻巧的文体,随笔可能不知不觉地遭受惰性的裹挟,无声地沉入世俗之渊。游山玩水,瞻仰古迹,缅怀故人,诉说乡愁,大量随笔自得其乐地穿行于这些话题,循规蹈矩地抒情议论,絮絮叨叨、陈陈相因。然而,我的心目中,随笔的写作如同横渡日常生活的洪流:只有仰起头浮出水面,才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分析始终是一种严肃的思想姿态,而不是纵容作家信笔随波逐流。

《文明七巧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我对于随笔的写作大致保持“三有”:第一,有想法。切忌有闻辄录,不分轻重,至少必须显示出不同凡俗的想法,若干异于他人的感觉。第二,有趣味。不久之前发表一篇考察“趣”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论文。“趣”不同于情,区别于理,而是分布于二者之间的广阔地带。诗歌的情感如同燃烧的烈焰,论文的理论坚硬严谨,随笔倾向于“情趣”或者“理趣”。第三,有情怀。无论是阐述义理抑或陈述事实,随笔必须显现出襟怀气度,小处入手而展示大视野。当然,所谓的情怀远远超出了写作的范畴,正如古人所言,“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作者张帆,笔名南帆,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