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申记珂罗版印刷所

郑振铎(1898-1958)
刘哲民在《回忆西谛先生》中说:
“(1952年秋)珂罗版印刷在上海硕果仅存两家,一是戴圣葆的申记印刷所,一是胡颂高的安定印刷所,差不多都是靠印西谛编的图籍维持营业的,如能迁京归入国家编制,可以一劳永逸。”
赵家璧在《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中也说:
“还有一位专印珂罗版的戴圣保,开了一家仅有两架珂罗版机的印刷厂,也一直替郑振铎印版画;后来就搬到庙弄郑振铎寓所的底层,振铎还帮他添置了两部印刷机,专印各种艺术画册。”
本文拟对郑振铎和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关系,以及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发展历程和印刷品略作考论。
一
郑振铎文集中的申记珂罗版印刷所
郑振铎的文集,涉及戴圣保和申记的地方颇多。
在《跋〈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郑振铎提及与戴圣保的一次合作:
“我忽然想起,葱玉在战时曾经把他的藏画摄照过一份照片,何不利用这一部分照片,先把他所藏的复印出来呢?这也许比较的轻而易举。过几天,去问当时负责照相的钱鹤龄先生。他说,那一份照片还存在他那里,不知坏了没有。我们随便捡了一张邵弥的《贻鹤图》给戴圣保先生去制版。不久,印样送来了,却是那么精美,差不多深浅浓淡之间,与原作几无甚差别。我高兴极了!觉得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比起日本人的印刷来,也差不了多少。”
在《〈伟大的艺术传统〉序》中,郑振铎也念念不忘戴圣保的功劳,他说:
“摄影者钱鹤龄先生,珂罗版的制版印刷者戴圣保先生,彩色版制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倾其全部心力从事于这个工作。较之我从前印出来的《域外所藏中国画集》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印刷方面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这表示:新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和印刷者是如何的忠诚而丝毫不苟的花心力于他们的工作和事业上。”
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最早出现在郑振铎的日记中,是1947年4月10日。很简略,只有“申记来”三个字。4月14日,又记有“申记来”,过了三天,又记下“申记送《图谱》来”。可见,郑氏和申记的合作大概始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印制。这套书刚开始是交给安定珂罗版社印刷的,后来,可能是印刷工作量大,也可能是安定的印样不能让郑振铎满意,郑氏把一些印刷任务交给了申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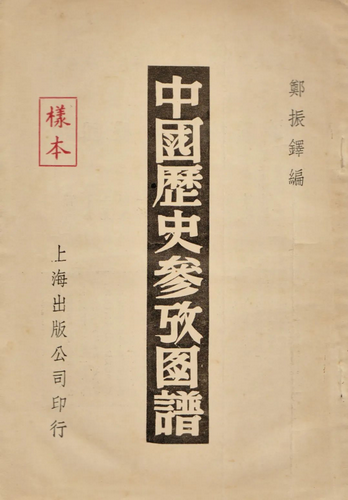
郑振铎编珂罗版精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征订样本
申记的印刷质量逐步赢得郑振铎的信赖,1947年6月2日,郑氏见到已印竣的《西域画集》,难掩兴奋,在日记中写下了“绝佳,甚可满意,此即辛劳之报酬也。”此后,申记的印样每每让郑振铎兴奋不已。6月6日,“申记送样来,绝佳!极高兴!”6月12日,“申记送印样来,甚为高兴!”7月12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10月12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11月11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甚至戴圣保过来“算帐”,他也“颇为兴奋”。他对戴圣保的称谓,也从毫无感情色彩的“申记”、“印刷者”,变成了较为亲昵的“圣保”。
赵家璧说郑振铎帮申记添置过两架印刷机。从日记看,这种帮助并不是无偿的。1948年2月4日,郑振铎记下了:“晨,圣保来,云,又定妥了一部机器,需要借款若干。”
日久月深,郑振铎和申记之间也难免有不愉快。
或因戴圣保爽约,如1948年4月12日,“候圣保送印样,竟不来,甚不高兴!”
或因印刷质量不如人意,如1948年5月20日,“圣保来,《唐五代画》已全部印毕。《陶录》的样张也已送来,印得不大好,颇不满意。”
最让人闹心的还是印刷进度,1948年有一段时间,为《汉晋画》迟迟不能印竣,郑振铎烦闷不已。4月14日,“阴,心里闷极了!和天气同样的灰暗!画集老印不出,一半也为了天气关系,很不痛快!”4月17日,“此辑印刷得还不坏,惟不知如何,竟印得极慢。预计月初可以出版,到了半月后,还不曾完全印好!”4月20日,“因为《汉晋画》迄未印齐,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来取书者甚多,均婉辞对付之,甚见痛苦。”4月21日,“晨,圣保来,《汉晋画》迄未完工,颇为不痛快!”4月22日,“《汉晋六朝画》至今未印全(除了五十部外),甚以为奇!心里很不痛快!”4月24日,“晨,到愚园路申记印刷所,观其印刷情形。去时,一肚子的气,为了圣保实在把《汉晋画》印得太慢了。但见到他们,却也无法生气。”4月28日,“晨,圣保来。《汉晋画》仍未印毕,为之焦急不已!”
在给刘哲民的书信中,郑振铎也多次提及戴圣保。后面会论及,此处就不一一枚举了。
关于印制《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郑振铎有一段回忆,既可以管窥印刷工作的艰辛,也可以蠡测他与戴圣保等人的密切关系,故迻录于兹。“珂罗版印刷,全是使用手工的。为了设备不够,气候的寒暖和阴晴,都会影响到图面的好坏,配料和油墨的良窳,也影响到图面的清晰与否。有时,一张图版印好了,发现了模糊等短点,便重行制版。有时,原书图片本来模糊不清,只好设法另行访觅比较清晰的。实在找不到第二来源的时候,方才勉强的用上原来的那一张。这其间的每一过程,也都是我自己和印刷工人们商酌、讨论的。有什么缺点,特别是在技术上,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二
申记的发展历程
戴圣保的名字,一作戴申保,《中国古代陶塑艺术》1954年6月初版,版权页即署“戴申保”。申记珂罗版印刷所,亦名戴圣保珂罗版印刷所、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如《中国古代陶塑艺术》1955年6月改订版,版权页上就是“戴圣保珂罗版印刷所”;《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版权页上印作“申记珂罗版印刷社”。
戴圣保还有一个兄长叫戴申昌,也从事印刷工作。郑振铎1948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他,“圣保之兄来了,带来了厚玻璃五块,即付之五百万,替他购下。”据秦廷棫说,他们“都是从商务学的技术,后来也都加入到真赏社(艺苑真赏社)。”戴氏兄弟为何离开商务?我想有必要引一段刘雪堂(他多年从事珂罗版印刷,对这一行业相当了解)的回忆,“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衰退,珂罗版印刷也同其他印刷工种一样受到摧残。当时,除了由杨信德主持、官商合办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由于它的原稿系宫内珍品,民间少见,因此销路尚好以外,别的珂罗版印刷所大都处于萎缩停顿的状态。上海的有正书局、中华印刷厂等的珂罗版印刷相继停办。仅存的商务一家,1937年毁于战火,次年在南京西路重建,但到了1941年也宣告停办。”由此,可以推测戴氏兄弟离开商务的原因和时间。
申记的开设当在抗战期间,据刘雪堂说: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技术工人为了谋生糊口,办了几家弄堂小厂,用手摇机勉强进行生产,艰难度日。如上海的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天一厂、安定珂罗版印刷社等。由于当时的工价低、条件又差,所以业务不振,技术下降,珂罗版印刷已日趋衰落。”
申记和安定这两家珂罗版印刷的“弄堂小厂”,在抗战胜利后,得到郑振铎的大力扶持。据刘雪堂说:“郑振铎到上海创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编审会,编印一些资料,要用珂罗版印刷插图,并设法资助申记和安定两个珂罗版作坊,增添了几台机器,珂罗版印刷的技术才得以保存下来。”胡颂高的说法也可作辅证,他说:“郑振铎到艺苑真赏社看到珂罗版字画印得好,就找到我,对我说无论如何要把珂罗版印刷行业保持下去,后来生意差,他还嘱咐戴申葆每月给我贰百元,维持住这项工作。”
1949年之后,申记独立存在了很长时间,1956年以后,它才从印刷史上消失,当然,也可以说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申记的最后归宿,按刘雪堂的说法,是并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分社。他说: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很重视这项特种印刷技术,积极扶植珂罗版印刷的发展。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出版部门应用珂罗版印刷出版图书,从此业务大有起色。1956年公私合营时,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安定珂罗版印刷社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分社,招请了一些技术工人,在永嘉路建立珂罗版车间。次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珂罗版车间将迁北京,上海为了保存此工种,留下了几名老年技工,又招收了一些青工,在原址成立车间,划归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当时称实验室)领导。”
刘哲民的说法略有不同,他说申记和安定两家珂罗版印刷所“差不多都是靠印西谛编的图籍维持营业的,如能迁京归入国家编制,可以一劳永逸。所以搬迁不成问题,主要是谈器材作价,工薪待遇等条件。几经磋商,最后还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来沪商定,开文制版所和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全部迁京,归入故宫博物院。安定则由上海市出版局安排,归入上海印刷研究所。”
鹿文波的开文制版所迁京颇为顺利,至迟到1953年底就完成了,而戴圣保的申记入京却颇多波折。
我们可以读读郑振铎的书信。早在1952年,他就有将上海珂罗版印刷工人和设备迁京的想法。1952年11月20日,他写信给刘哲民,说:
“珂罗版的印刷,在北京极为需要。明年要大规模的印些珂罗版的书籍。希望能和胡颂高及戴圣保商量,他们能否搬到北京来?我们可以使他们加入博物院的印刷部门工作。工人多些也不妨。只要有技术的,我们都可以要。(政治上可靠!)我们正在考虑:(一)他们的待遇问题,(二)如何收购他们的印刷机?(三)搬家的费用,如何付法?可先行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有一家,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已经关了门,不知工人尚可找得到否?为政府工作,是很有远大的前途,并且是很有意义的。一切物质的条件,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不过分。”
这之后,至1953年7月13日,郑振铎给刘哲民的书信,一直念兹在兹,不断的催促戴、胡北上,他甚至对戴、胡等人的薪给和安家费都有很具体的考虑。不过,1950年代最是风云诡谲。相隔一月有余,戴、胡进京的事突然被搁置了。8月26日,郑振铎有信给刘哲民,说:
“戴、胡印刷所迁京,迟迟未曾解决。现在情况有一点变更,希望他们暂时不要来,什么时候让他们来,以后再通知。关于他们的印刷工作,要他们放心!这里要印的东西不少,当可不发生影响也。见到他们时,乞代达歉意!并告知:所有故宫印珂罗版的事,仍委托他们办,每月决不至落空。不过,不必在北京印刷耳。”
当事人胡颂高有段回忆,可与郑氏书信互相印证,录于兹。“解放后郑振铎要我去北京,因为没有房子,便介绍我先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到印刷试验室,后并到市印刷技术研究所。北京还要一个人,戴申葆就去了。他退休后还住在北京,今年已七十八岁了。戴申昌到科学出版社做工,我到北京戴还接待过我,后来他调到文物出版社。”
综上可知,戴圣保入京的事,尽管有一些波折,最后还是落实了。不过,他是随人民美术出版社珂罗版车间迁京的,还是调入了故宫博物院印刷所,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
申记印刷品知见录
申记印的书,今日已难得一见。我于20世纪的珂罗版印本,颇事涉猎,惟书囊无底,不能一一罗致案头。兹将历年所见,胪列于兹,尚祈博雅君子增益校讹,匡我不逮。

《浑源彝器图》
《浑源彝器图》,商承祚编纂,八开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6年6月出版发行,上海申记制版印刷所代印,京平沪各大书坊代售。定价(不含寄费)洋纸国币三元,夹连国币二元。这是目前所见,申记最早的印刷品,从版权页可见申记当时的地址是上海康脑脱路六三三弄三三号。前系篆书题耑,并楷书“民国廿五年六月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
《南阳汉画象汇存》,孙文青编纂,商承祚校订,八开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7年6月出版发行,上海申记制版印刷所代印,京平沪各大书坊代售。定价(不含寄费)国币八元。前系商承祚篆书题耑,并楷书“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前有孙文青序言两篇,后系商承祚跋文一篇。
《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郑振铎编辑,钱鹤龄摄影,共二十四辑,八开,初印本为活页,函套装,由上海出版公司发行。我见过其中三种初印本,以《西域画》(上中下三辑)面世最早,于1947年9月印行;《汉晋六朝画》1948年1月印行,《明遗民画》1947年12月印行,印数都是200套。据刘哲民说:“《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共二十四辑,搜集资料和编辑工作花费了一年多工夫,首为《西域画》,次为汉晋六朝画、唐五代画各一册,宋画、元画、明画各三册,明遗民画二册,清画四册,续集四册,约共一千三百余页。”参与这套书印刷的有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安定珂罗版社、天一珂罗版社。
《中国版画史》(图录部分),计划出六辑,共完成五辑,第六辑只出版了一册。据刘哲民说:“已完成的图录部分五辑,成了艺术家、藏书家的瑰宝。这五辑,都是西谛自编自印的。印刷全由戴圣保的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承担,技术是精美的。其中一至四辑十六册,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发行。第五辑四册一套,一九四七年印刷完成,由上海出版公司发行,实际上是西谛自己发售预约,由旧书店代卖出去的,总数仅二百部。”又说:“《中国版画史》的第六辑,后来由戴圣保、胡颂高合印成《搜神广记》一册。其余三册,解放后西谛一再提到预备把材料整理好,抽暇编成。终于因各种计划的牵制,未能编完。逮珂罗版印刷所迁京后,更缺乏印刷条件,《中国版画史》终成金瓯之缺,使爱好版画艺术者永在怀想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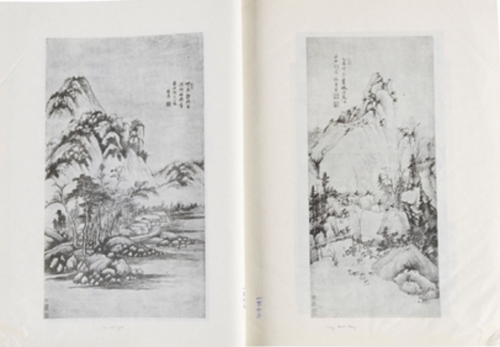
《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内页
《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郑振铎编辑,钱鹤龄摄影,共二册,四开本,1947年上海出版公司发行。据刘哲民说:“这部画集印得非常辉煌,四开本,有精装、平装两种,精装本用夹贡纸珂罗版精印,织锦封面高背装,平装本用宣纸印,柿青纸面双丝线装订。这样大的开本,国内图籍从未见过,只有日本出版的画集偶一有之。”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非卖品),八开本,共二十四辑,图版六百十八页,收图片三千零三幅。印刷出版工作始于1947年,1951年4月完成。这套图书的版权页上有出版机构为上海图书公司,并未标明印刷机构,但郑振铎日记1947年4月2日有“安定胡君送印好之《图谱》来”,4月17日有“申记送《图谱》来”,可以确认安定和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承担了此书的印制工作。此书版本较多,有重磅木造纸单面印刷,八开活页,函套装;有重磅木造纸单面印刷,八开活页,24袋袋装;有宣纸双面印刷,八开,24册线装;有日本道林纸双面印刷,八开,3册洋装。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郑振铎编辑,共十二辑,八开,初印本为活页,每辑一个函套,整套书另配有木制夹书板,板上有宋体凹刻书名,1952年7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印数1000部。此书后来不断再版,到1955年印第五版的时候,珂罗版部分,依然由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承印。后来郑振铎还编辑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却因故未能付印。按刘哲民说法是因公废私,“动议开文、申记、安定迁京,正当西谛筹划编纂《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预备付印之时。一旦国家需要,他毫不考虑个人的计划,而是竭尽全力急国家之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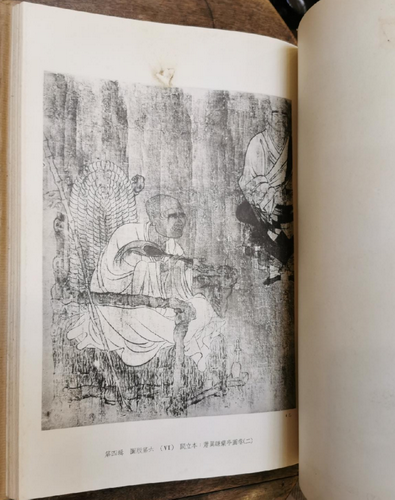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内页
《楚辞集注》《楚辞图》,这两种书,由申记和安定承印的,大都被当成礼品,赠予国际友人,最是少见。《楚辞集注》,大十六开本(长32厘米,宽20.5厘米),一函六册,蓝绫封面,白绫标签。首册有牌记页,文字为毛笔楷体,“人民文学出版社景印北京图书馆藏宋端平刊本,版匡尺寸悉照原书。共印五百部,此为第□□□部。”此书日本读卖新闻社曾翻印一千部,装帧、开本,包括牌记都无区别,现今书肆所见,多为此种翻印本。《楚辞图》,装帧、开本同于《楚辞集注》,牌记文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景印,共印五百部,此为第□□□部。”中华书局1963年曾将此书重印三百部,一函二册,版权页标明“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原版”。郑振铎特别关心这两种书的印刷,他先后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觉民和文怀沙去上海,与刘哲民共商印书事宜。他还一再过问印书的进度,并强调“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对印出的样张和样书,他不仅提出了改进意见,还亲自校改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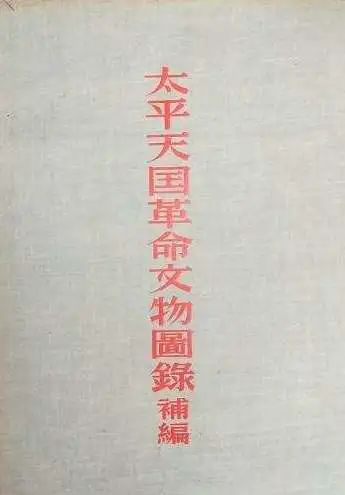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郭若愚编,群联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总经售,大众制版工业社有限公司制版,昌新橡皮印刷厂和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承印,定价12元,印数620部。
《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梁岵庐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售,1954年12月初版,印数2000部,定价30000元(旧币)。
《中国建筑史参考图》(非卖品),刘敦桢编辑,陈从周校订,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和同济大学建筑系合印参考资料,1953年版,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制版印刷。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秦廷棫著,艺苑真赏社经售,1954年6月初版,图版70页,印数140部,定价200000元(旧币)。此书1955年6月出版改订版,图版68页,印数400部,定价20元。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发行,五尺夹宣五开本,二册一函,1955年9月初版,由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和安定珂罗版社共同承印,定价38元,印数1000部。
《何香凝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发行,1954年9月初版初印,由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和安定珂罗版社共同承印,定价50000元(旧币)。1954年11月和1955年2月,又印刷了两次,第二次加印了3200册,第三次加印了2000册,定价不变,印刷却都是申记独立承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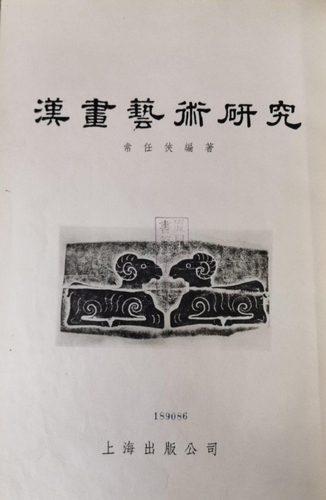
《汉画艺术研究》
《汉画艺术研究》,常任侠编著,八开本,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12月第一版,由安定和申记承担珂罗版印刷,定价17元,印数为380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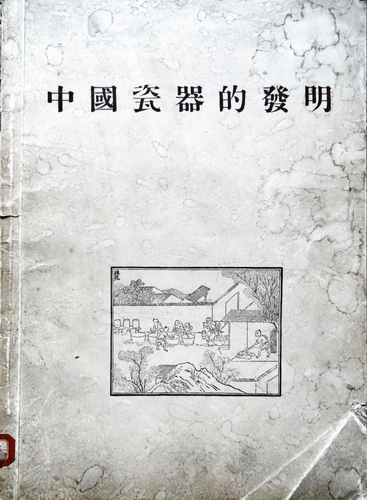
《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瓷器的发明》,蒋玄佁、秦明之著,八开本,公私合营艺苑真赏社1956年初版,定价16元,印数为200部。此书1957年曾经重印300部,印刷者已经变成了中科艺文联合印刷厂。
《模印砖画》,郭若愚著,艺苑真赏社出版,1956年5月修订版,图版28页,印数500部,定价4元。(附记:此书初版印刷时间是1948年6月,出版时间是1954年10月,由安定珂罗版社承印,印数200部,有两种不同的本子,道林纸本60000元,料半纸本40000元,都是旧币值。)
此外,由傅惜华编辑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1950年出版)和《汉代画像全集二编》(1951年出版),虽然标注图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但这两部书很可能也是由申记或安定承印的。有两条依据:其一,当时的上海只有申记和安定两家珂罗版印刷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不可能找到第三家。差不多同一时段,申记为上海出版公司印刷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也没有标注申记印刷所。《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预约样本的封面上甚至还印有“上海出版公司印行”的字样。可见,当时出版物上标注的印刷机构未必属实。其二,郑振铎1953年9月21日有信给刘哲民,说:“闻汉学研究所仍拟印《汉代画像全集》第三集,请转告戴、胡,不能承印此种书籍。因帝国主义者的印件,我们现在决不可代印!同时,戴、胡二人的印刷力量,我们可以完全包下来。不可能有力量再去承印那些书也。此事至要!”20郑有“再去承印”之说,说明《汉代画像全集》的前两集很可能就是戴、胡承印的。
四
余论
本就有蠹鱼之好的郑振铎,在抗战爆发之后,更是以“保卫民族文化”为职志。他痛心于“自八一三以来大江南北之文化扫地以尽”,大声疾呼:“有力者,有理智者起来!在这最艰难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在他看来,收罗国家徵献,是另一种为民族效劳的方式。“夫保存国家徵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

郑振铎任文物局局长时的证件
保存国家徵献,保护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收书,还要印书(翻印珍稀古籍)。至迟在1934年,郑振铎就对印书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他写过一篇《向翻印“古书”者提议》,后来又发表过一篇《再论翻印古书》。他已经清楚的意识到,“至于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语》之类,那也是就个人性之所近、嗜好之所在,随意为之,没有人可加阻止——也许还该加以赞颂。不过,也不宜印得多,不宜纯为了营业的目的。”他希望仿效日本人,用珂罗版影印中国珍稀古籍。
1940年,郑振铎联络同人,组织了“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收书之际,也擘画印书事宜。这年10月24日,在提交给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第五号工作报告书》中,他说:“此间诸友均主能将孤本、善本付之影印传世,我辈亦有此感。惟石印甚不雅观,宋本元椠,尤不宜付之雪白干洁之石印。至少应以古色纸印珂罗板。所谓古逸,确宜以须眉毕肖为主。”郑振铎从来都是实干家,《第六号工作报告书》就可以看到他为印书所做的准备。“印书事,正积极进行,现已购得纸张六百余元,储以待用。第一步拟先印书影,一以昭信,一以备查,且亦可供学人应用。此外,拟再印行甲乙种善本丛书若干种;甲种善本拟用珂罗板印,照原书大小(较续古逸为壮观)。”及至《第七号工作报告书》,他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印书了。“印书事,因纸张已于去岁冬间购备若干,故进行尚为顺利,不受物价高涨之影响。应印之书,约有四五十种。……书影亦已陆续在印。……珂罗板以印于古色纸上者最为悦目。现已设法向泾县造纸处设法定购古色宣纸。(不漂白,价且可较廉。)将来,凡印珂罗板之善本书,皆拟用此项古色纸印刷。”
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与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合作,可以说是他“保存国家徵献”活动的延续。除了申记之外,郑振铎和上海的另外两家珂罗版印刷机构,安定珂罗版社和天一珂罗版社,也有过较密切的往来。
郑振铎早年曾经主编过一套《世界文库》,致力于引介外国文学名著。1940年代以后,则偏重于历史、美术类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在给刘哲民的一封信中,他说:“惟我们公司(上海出版公司)的将来,还在历史、美术一类书的出版上。这是独门生意,没人能够竞争的。”郑振铎所说的“独门生意”,一方面是资料上占优势。版画和美术图册是郑振铎藏书的一个着力点,所以,这一类的出版素材,其他出版机构难以企及。另一方面是印刷上占优势。抗战胜利后,上海仅存的三家珂罗版印刷机构(申记、安定、天一)都为郑振铎印书,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不是短期可以建立的。
其实不止郑振铎,很多新文学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都不同程度的涉足过美术出版。他们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让他们编辑或策划的美术出版物有着更为广泛的受众。他们不同于艺术家的出版视角,让他们选择的美术书籍更具穿透时空的价值,甚至在某些领域开风气之先。考察他们的美术出版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的艺术传播和艺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