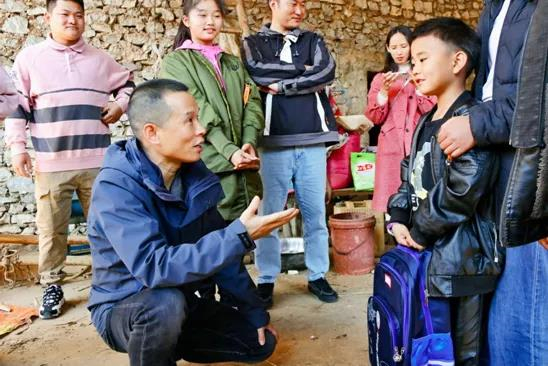一树海棠 一代风华
——记嘉定名人、民进会员作家秦瘦鸥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以译作《御香缥缈录》声名鹊起;40年代初又因创作“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红遍全国。《秋海棠》曾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感动了千千万万多情男女,而小说的作者就是从上海嘉定走出的一代文化名人——秦瘦鸥。
痴迷戏曲, 走上文学道路
他说:“我不过就是一个戏迷”。
1908年6月28日,秦瘦鸥出生于上海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嘉定。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须发皆白的祖父。他在自传中回顾,五六岁时便迷上了嘉定草台班演出,觉得看戏是最开心的事了。后来,他来到上海十里洋场读书,上大学了,恰逢昆曲传字辈艺人来上海演出,他竟像他祖父热爱昆曲一样,看演出入了迷。经常把所有的零用钱都买了戏票,有时甚至让自己买牙膏的钱都没有。他还亲自到一家“逸社”的票房学习武戏,买了花枪、薄底靴苦练。有一次他练习抡背,摔得太猛,把床上的棕绷也摔断了。家里的东西也屡屡被练功的他打碎。后来在母亲的极力反对下,他才不得不放弃。大学毕业后,他得到了一个铁路局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这样的职务等于是捧上了一只“铁饭碗”,也是人人羡慕的一份“美差”。但是,秦瘦鸥却并不喜欢这个“美差”,由于儿时看过许多戏,戏里的唱词经过千锤百炼,很有文学性,虽然他没能唱戏,但爱屋及乌,喜欢上了文学,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为报刊写文章,从此走上文学道路。
几番波折,留下传世佳作
因为喜欢看戏,秦瘦鸥认识了许多名角儿,也目睹了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后来,在他当了一名记者后,更是与京昆界的演员来往频繁,在长期接触中逐步了解到京剧艺人的真实生活。1927年初,上海新舞台有两位京剧青年演员,在天津与奉系军阀的姨太太交往密切,被军阀抓走连夜枪杀,临刑前,军阀为了发泄他的余怒,用大刀在死者脸上乱划一通。这一事件轰动全国,引起国人极大愤慨。当时秦老的内心非常激动,就以此为素材,又综合了其他京剧艺人的遭遇,加以概括和提炼,写成小说《秋海棠》。
1929年间,秦瘦鸥结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并向其投稿。几个月之后,他把小说《秋海棠》厚厚的一叠稿笺,面交独鹤,不料,却是音讯全无。隔了3个月之后,独鹤把《秋海棠》原稿交还。
但这次的挫败,并没有击垮秦瘦鸥。后来报馆方面要求他再写一部小说,他就拣出旧稿《秋海棠》把它重新整理,悉心改写。小说最初是想给《大公报》的。可是随着“八·一三”事件的爆发,《大公报》和其他各报都临时加出号外,取消副刊,登载战时消息,于是《秋海棠》的事便又搁了下来。之后的三四年间,秦瘦鸥不断修改《秋海棠》,直至1941年在周瘦鹃主编的《申报·春秋》上连载,引起轰动。小说不仅马上出了单行本,还被改编为沪剧、越剧、话剧、评弹等众多戏剧形式,不久,又被搬上了银幕。京剧界的艺人们看了《秋海棠》后,认为小说说出了他们的惨痛遭遇,把他们看作自己真正的朋友。而且《秋海棠》不仅仅是揭示封建军阀的荒淫无耻,更重要的是加重了抗日爱国主题的宣传,巧妙地把爱国情操贯穿在小说中。张爱玲发表于1943年11月《古今》半月刊上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文,就极称赞秦瘦鸥的《秋海棠》。她说:“《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
现代文学评论家陈子善说:假定秦瘦鸥没有写过其他作品,就单凭一部《秋海棠》,就在文学史上站住了。
一树海棠,成就了秦瘦鸥先生的一世风华。
笔耕不辍,书写一生报祖国
秦瘦鸥先生笔耕于小说、诗歌、杂文、新闻、评论等文学艺术领域,卓然成家。
他在大学求学时期,就撰写出版短篇小说《恩·仇·善·恶》,这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21岁又替《时事新报》写了长篇连载小说《孽海涛》,从此与小说结下不解之缘。30岁之后,更是天南地北奔走于桂林、贵阳、重庆、香港等地办报纸、写小说。无论何时何地,秦老从未停下过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秦瘦鸥受到批斗,曾想与老舍、傅雷一样以死抗争。在一次野蛮的街头批斗会之后,人群中有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低声劝慰,秦瘦鸥从读者的理解和爱护中得到安慰,终于走出了绝望的泥沼。在干校劳动时,他常偷偷地在香烟盒背面或练习本上写小说草稿,这就是后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劫收日记》。吴承惠在回忆秦瘦鸥的文章中说:“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我被调回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与秦老合作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不但自己写稿,还帮我们发现新作者,像被秦老爱称为‘咪咪’的华文漪,就给我们写过一个时期的艺术生活小品。还帮我们审看读者投来的长篇连载,看后必附来密密麻麻的两纸,上面写着故事的梗概,审看的意见,是用还是不用的建议。”
1982年,秦瘦鸥迁入法华镇路淮海大楼新寓。他虽已高龄,又身患顽症,仍经常参加街道里弄的活动,替邻里向街道或区政府写信,反映社情民意,还为近邻学子辅导高考作文,指导写作,并给收入低微的里弄清洁工以接济,受到居民们称道。秦瘦鸥还担任家乡嘉定京昆艺术研究会、七色文学社等文化团体的顾问,并将收藏的文史资料和书画捐赠给家乡的文化机构。
创作之外,秦瘦鸥还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据说中国第一本《茶花女》也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的,他从法文版《茶花女》直译过来,由春明出版社出版,可见得他还懂得法文,可惜连他的家人至今也未能见到这个译本。除此之外,还翻译了晚清德龄女士写的《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等。
秦老晚年,虽已年迈体弱,却仍“壮志不随华发改”,积极写作和参加一些学术和政治活动。多年来,他为促进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应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的邀请,做了两次《昆剧的成长及其特色》的学术报告;在有关报刊陆续发表散文、诗词、文学评论等100多篇文章。他还打算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王则起义》,更有写《秋海棠》第三部续集的愿望。他多次表示,在他暮年之际,要争取多写些作品,为发展祖国的文学艺术和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1990年初夏,嘉定教师进修学院的姚济民老师去拜访秦瘦鸥先生,此时的秦老衰老多了,显得很是瘦弱,却还在顽强地写作。1993年春节后,有关部门将写好的有关他的《传略》寄给他斧正,他还给了回信,对被列入革命文化名人表示高兴,并仔细审阅修改了稿子。但其信笔迹显得紊乱无力,可以想见他书写时,手是颤抖的。半年后,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如今,这个修改稿还得以保存着,令人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看到这本《上海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秦瘦鸥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秋海棠》《危城记》《梅宝》《第十六桩离婚案》《永夜》;电影文学剧本《江淮稻粱肥》;散文集《晚霞集》《海棠室闲话》《戏迷自传》;评论集《小说纵横谈》,札记集《里读杂记》,短篇小说集《第三者》,译著《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茶花女》等。长篇小说《劫收日记》还获得了湖北省最佳长篇小说奖。不过,每当人们提起这位海棠室主的时候,总是忘不了要说一句:他的《秋海棠》了不起啊!
1993年10月14日,秦瘦鸥走完了他的一生,与世长辞。但是,他的“秋海棠”却会永远活跃在舞台上、银幕上;其影、其言、其书也将永远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