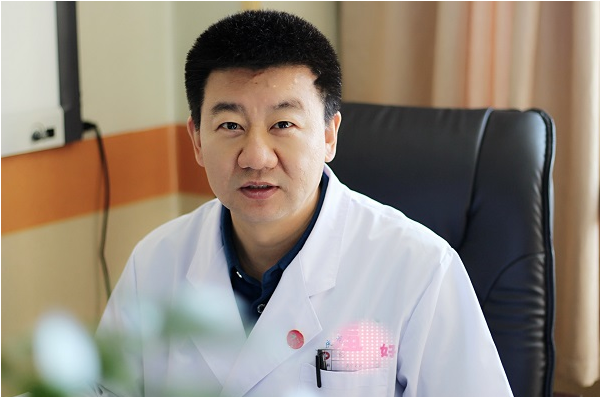一个江南乡村望族的家国情怀
南宋建炎年间,开封府陈留县田家庄的一支田姓家族,始祖田晟,官至司徒、鲁国公。其子田秩扈跸南渡,以功授大司空,爱山阴欢潭之胜遂卜居焉。
——《欢潭田氏宗谱》
(一)
让时光定格在890年前。
那是赵宋之世由北宋向南宋过渡的历史大变动时期。那是一个风云激荡、沧海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令人难忘的时代。
而掌控时代命脉的无疑是大金国。
公元1126年秋,金国灭辽国后乘胜南下,整个中原顿时烽烟四起。次年一月,汴京(今开封)城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五月,在外组织勤王兵马的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为不给新政权喘息机会,1127年秋,金朝分兵攻宋。十月,高宗南逃扬州。金人又于次年兵锋指向扬州。1129年二月,高宗自扬州至镇江。闰八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至临安。1138年(绍兴八年),南宋正式定行都临安。
在大宋王朝节节败退的过程中,大宋子民为躲避战乱,抑或响应政府的号召蜂拥南迁,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大迁移。在这支官迁的大军里,就有开封府陈留县田家庄鲁国公田晟的儿子田秩一族。因护着高宗皇帝平安到达临安有功,被封为司空。后因爱山阴天乐乡欢潭山水之胜,遂卜居于此。田秩被尊为欢潭田氏家族的始迁祖。后代在村内建有大司空家庙以奉祭祀。
(二)
世易时移。
田家庄今在何处?昔日家园是否依旧?始祖留居陈留的后裔生活可否安好?带着先辈和族人们几个世纪的忧虑、企盼,公元2018年9月,由笔者及宗亲一行五人专程赴河南开封,踏上了陈留寻根问祖之旅。
(三)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上的谜团,总会有人去探索,去追寻,这往往需要借助于史书、地方志、族谱、家乘,乃至于碑文、墓志铭的释读,也许这就是史志的魅力所在吧!
在陈留镇政府会议室,常年致力于开封历史研究的文物保护专家、开封市祥符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陈文斐对我们侃侃而谈,娓娓道来。
陈留修志源远流长。明代陈留县志纂修居河南所有明代方志之首,此县志为知县蒋时行修,书久佚。清代于顺治、康熙、宣统三朝凡三修,书均存。
关于陈留,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诉说,有太多的宝藏可以挖掘。
陈留,春秋时为留邑,先属郑国,后被陈国所得,故有其名。自西汉开始,先后做过700余年的郡国之城。而作为县治更有两千余年之久。著名宰相伊尹,文学家、政治家蔡邕,洛阳令董宣均是陈留人;东汉刘协、西汉张良、三国曹峻都曾在陈留居住。汉末曹操起兵陈留,讨伐董卓,控制了刘协,“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封曹氏王。“中华姓氏看中原,中原姓氏看陈留。”孙中山先生的祖籍地在陈留,已成客家人公认的事实。2012年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还曾到陈留拜祖认宗。……然而,随着北宋定都汴京,陈留慢慢地淡出历史。1957年,陈留县被撤销,并入开封县。先后设陈留人民公社、乡和镇。2014年10月,开封县升格为祥符区,这样,如今的陈留仅仅是开封市祥符区所辖的普通一镇。
与开封地脉相连的“陈留”,不应该永久沉寂。
(四)
历史,变幻莫测;生命,生生不息。
根据开封市祥符区民政局和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区内田姓聚居的村落在近距陈留古县城约20公里左右的曲兴镇东田村东田寨自然村和门八府村西田寨自然村,而如今的陈留镇已找不到田姓聚居的村落了。
翻阅清康熙三十年《陈留县志》,在“城池”卷载有“县旧有四坊,三十五保。燹没后,……仅存其九,曰高阳、曰白邱、曰长岗、曰潘岗、曰芦村、曰河口、曰大尚、曰清流、曰两张、余尽名存实亡。自垦荒之令下,招集屯民,又立一保,曰鼎新,共为十保。”
在“附保坊”中,查到田家庄共有两处:一处隶属清流保,一处隶属潘岗保。但东田寨和西田寨这两个村名没有查到。
翻阅清宣统二年《陈留县志》,在“城池”卷载有“旧志,保分为十。后境内渐增为十八,境外又增其二,曰南九保、曰北九保。南九保:莘、白、高、雨、水、韩、小、韦、槐是也;北九保:潘、堌、鼎、河、芦、长、清、大、堤是也;境南境北两保,名虽属留,而赋税多附属于邻封,且保数因村庄而增。”但在“附保坊”中,已找不到“田家庄”这个村名了。通览其志也均没发现“田家庄”这一名称。只是清流保和潘岗保仍然存在。东田寨和西田寨两个村则在清流保所属村保中赫然在目。
(五)
那么,史志中的此东田寨和西田寨是否就是今东田寨和西田寨自然村呢?笔者又从方位间距中加以测算。
《欢潭田氏宗谱》、《田谨甫公亲缘名录》等族谱、家谱数次提及“田家庄去陈留县城三十里”。
曲兴集是陈留县一个较大的集市,也是一个村保。清康熙三十年、宣统二年的《陈留县志》中都载有“曲兴集,县东北五十里。”清宣统二年的《陈留县志》中还把曲兴集与东田寨、西田寨同列入清流保中。
清康熙三十年《陈留县志》中还多处提到潘岗、潘岗铺。“潘岗县北四十里,相传宋潘美故里。”“潘岗铺县北四十里,潘岗霁雪即此处。”
清顺治十六年《陈留县志》卷二中部记录了潘岗又称潘岗铺,俗称潘岗保,在陈留县城东北处四十里。是北宋时期潘美的府邸。潘美的墓,后来就建在岗侧。
可见,潘岗保和清流保不仅同属北九保,而且与潘岗、潘岗铺、潘岗霁雪景点及曲兴集、东田寨、西田寨等村保均同在县城以北或东北,大致五十里范围之内的位置。
陈留古有八景:桃洞云霞、睢水秋波、寿寺晨钟、谯楼暮鼓、柳堤烟雨、莘野春耕、仓城晚牧、潘岗霁雪。潘岗霁雪,是陈留八景中唯一一个在县城外的景点。这里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北宋开国初年,潘美奉旨带兵抗辽东征,路过潘岗,初秋时节,只见树木花草郁郁葱葱,风景宜人,便在此扎营。在抗辽东征凯旋回朝之时,又路经此地,此时正值冬季,这里银装素裹、分外宁静。不知道是打胜仗的心情好,或是这里的风景美。潘统帅高兴地对部下说:“天色已晚,又遇下雪,离京城五十里,今晚在此宿营。”随后又感慨道:“要是我的府舍建在这里该多好呀!死了埋在这里都乐意。”等到潘美告老还乡时,经皇帝恩准,果真在这块高地上安了府舍,死后埋葬于此。据当地有文化的一位老人回忆:岗上原遗留两座关帝庙,大殿两旁柱子上依稀可辨二幅对联。上联是:赤面赤心千里怀赤帝,下联是:青竹青灯万年留青史。解放初期,庙毁。1958年大跃进平整土地,岗也被夷为平地了。
许是因为这里不仅景观美,宋代遗留下的题咏和艺文更为贵重,为景观增添美色。于是有了潘岗霁雪的景点。
说起潘美,许多人有点陌生,但是潘美就是戏曲里、小说中提到的潘仁美,众人就耳熟能详了。在开封人眼里潘仁美是奸臣,他陷害忠臣杨家将。杨家七郎八虎保大宋两狼山之战,老令公李陵碑阵亡。在战北国闯幽州之战中,杨家将为国捐躯的悲壮场面,催人泪下。杨家将的尽忠,让人们给对立面的潘仁美染上白脸。特别是箭穿杨七郎,更显出潘仁美公报私仇的奸臣嘴脸。
其实,历史上的潘仁美,大名府人氏。因降服陕西兵马大帅袁彦入宋,讨伐南唐取胜而受到宋太祖重用。宋太宗继位后,又在率部征服江南和夺取中原中屡立奇功,累官止中武军节度使,受封韩国公,算得上北宋的一员名将。潘杨两家的官司,除两家之间的恩怨外,更多是受宋代重文轻武主导意识及军事制度的制约,造成互不信任,矛盾愈演愈烈。这个责任究竟怨谁,事过千年,只有让大宋的寇准去断潘杨两家的公案。
(六)
在陈留镇政府,我们听完了镇长赵宏杰、副镇长胡长勉和镇党委组织委员毛薷媱的情况介绍后,又在祥符区政协办公室李海水主任的陪同下,驱车20分钟左右,来到了曲兴镇东田村。
在村民委员会会议室,村支书侯登政、村主任田景彦等村委会班子全体成员及村里田姓长者十余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大家就像久别重逢的一家人一样围坐而谈。
东田村现有青龙铺、吕寨、何砦、干河嘴、范店、东田寨六个自然村,全村人口3000多。东田寨约710人,有田、侯、赵、袁、李姓,田姓占百分之四十。63岁的田村长自豪地说,东田寨的历史比曲兴镇还早。如果要问田姓祖上从哪儿来,村里上年纪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回答,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片沙土地上。但祠堂、家谱等实物证据没有。兴许有过,也肯定被洪水冲走了。几百年来,村里已数不清发过多少次大水了,每发一次,回迁的老百姓凭记忆中的大致位置再圈地建村,代代如此。
大家还提到,相邻还有个西田寨,田姓人口还要多,都是同祖同宗的。现隶属于门八府村。笔者因为在清宣统二年《陈留县志》中看到过清流保下面有个田果寨,便问起。侯支书笑笑答,田果寨属曲兴镇双楼村委,不要以为寨名开头有个“田”字,可那里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为更详尽地了解情况,我们还专门联系了门八府村村支书耿振青、主任耿振武、村委兼会计田华柱。得知门八府村下辖耿砦、门八府、西田寨三个自然村。西田寨共有700余人,有田、程、朱、李四个姓氏,田姓人口占百分之九十。这里的田氏与东田寨一样,也是世居于此。历史上,东田寨原叫东田庄,西田寨原叫西田庄。以前,大概在大清朝之前吧,东田庄与西田庄是合在一起的,名叫田庄,史称田家庄。现在因为长久没发大水了,西田寨整个村就搬到黄河古大堤外面去了。
(七)
黄河之于开封,如同凝结在心口的蚌珠,是痛苦的结晶,也是精华的见证。
由于黄河冲出郑州邙山后,进入平原,落差骤然变小,泥沙大量沉积,致使开封段的黄河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增高,与此同时,两岸大堤也日增年高。今天黄河的河床底部已与北宋铁塔的第三层持平了。黄河被两岸大堤夹护着从开封城北高处汹涌流过,形似天河。“河底日隆堤日高,黄河竟是天上涛”,这是开封人对他们身边流滚而过的黄河的评价。
开封因黄河而兴,亦因黄河而衰。正是因了滔滔东流之水的种种便利,开封才有八朝古都的美誉。宋朝则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史书更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描述开封。“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顺口溜说的却是被黄河淹没的一座座历史上的开封城。今天龙亭公园地下分别埋着宋、金皇宫和明代周王府三座宫殿,就是由于黄河决堤在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不同地层留下的三个不同遗址。
清宣统二年《陈留县志》亦载:“大河入中国所经万里,而入于陈留之境者仅二里。则二里之河,其为利害与万里之长河,等也。”“考历来溃决之口,其在陈留之境者亦鲜,而被陷溺沦胥之害者,则同也。”自宋至清,黄河决堤不断,其中开封发生最大的两次水患分别在元大德初年和明洪武十六年,致使陈留境内平地行船。故“大约陈留之附开封为最近,开封之河患息,则陈留之河患亦息,开封之河患危,则陈留亦危;此固相从之势也。”
(八)
时令适值白露,仲秋的黄淮平原,夕阳西沉,凉风习习。从东田村返回陈留的路上,车子在田间里垄的村道上徐徐前行。望着不停掠过车窗的一排排白杨树,一簇簇玉米地,一片片间或种着大蒜、花生等农作物的焦泥沙土,不禁令人勾起阵阵思绪。这难道不就是900年前昔日家园的一幅农耕景象图吗?!
从史料记载里印证,从方位间距中推测,从黄河决堤、水灾泛滥发生村庄位移的可能性分析,从走访当地乡贤、田姓长者进行座谈调研了解,笔者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东田村东田寨、门八府村西田寨与宋代的开封府陈留县田家庄所在的地域方位基本相吻合。今天生活在这里的田姓基本可以确定是欢潭田姓始迁祖田秩的兄弟姐妹的后裔。
假如再往上,推到一千年前,二千年前,直至五千年前……
依据《华夏田氏考》碑记载:“炎黄为天下共祖。田完系华夏田氏始祖。黄帝至田完共五十三代。”最近从设在山东枣庄田完祠内的华夏田完文化研究会传来消息称,根据现有史谱资料已得出“田锡是田完的第三十七世”的研究成果。田锡,四川眉州洪雅人,北宋名臣,后迁居陈留,是陈留田氏的始祖。而《欢潭田氏宗谱》开篇记载的欢潭田氏第一世田晟,恰恰是田锡的曾孙。倘若果真如此,欢潭田氏整个家族世系图的脉络就非常清晰明朗了。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下篇
明永乐八年,徙浙巨姓实边,举族迁至陕西临洮府,尚有一子因出继未迁,后复归本宗,子孙繁衍,数又以千计。
——《欢潭田氏宗谱》
(九)
把时间回溯到600年前。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繁,终于爆发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1368年正月,义军首领朱元璋趁各路大军获胜之际,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明太祖。随即又进行了长达22年的统一战争。为确保王朝长治久安,1370年四月,他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藩王,分镇诸国。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故,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因恐诸王权势过大,便废削五王。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攻下应天,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
持续不断的战乱和涝蝗疫之灾使中原和长江流域人口大量亡徙。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促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明朝于1370年(洪武三年)至1417年(永乐十五年)的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全国各地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涉及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人数达数百万。据《明实录》载,仅浙江、福建、江西达二百二十七个县市。浙中欢潭田氏巨姓(包括家族中的家丁、丫环、佣人等)充边陕西临洮府,就是明政府生怕“大族相聚为逆”而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强制移民。
(十)
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地名演绎与历史的真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它反映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而有时却与本来面目大相径庭。
关于欢潭田氏巨姓充边临洮府,绍兴古戏和民间传说曾有《七星剑》的故事流传。但与真实情况完全是相左的一个版本。
《七星剑》的故事情节,绍兴古戏和民间传说大同小异。大致说的是,欢潭田氏到了十三世孙时出了一个恶霸式的人物,他欺辱民女、鱼肉百姓,恶名远扬。皇上便派钦差大人微服私访。田氏恶霸命家丁抓人搜身,结果从内衣中搜出钦差印玺。因恐其事发,遂把钦差打入水牢,欲置死地而后快。田家有佣人王嬷嬷,心地善良,又有正义感,便从熟睡的看守那里偷了钥匙,放跑了钦差。钦差逃离时,叮嘱王嬷嬷,“若有朝一日田家遭遇大难,你只要头戴蓑笠、手拿扫帚、身穿蓝布衫,站在桌子上,便无人敢伤害你。”钦差回到京城,上奏皇上。永乐八年除夕,钦差手执“七星剑”,奉旨查抄田府。兵围一村,凡有干系者,一律问斩,其余统统充边。田府抄家时,王嬷嬷惊恐万状中想起钦差临走时的嘱咐,便按钦差所言,忙站在桌子上,并将田家小少爷搂于怀中,推说是自己的干儿子。从此田氏家族只留下王嬷嬷救下的这一脉。
(十一)
翻阅《欢潭田氏宗谱》,有关充边临洮的记述只寥寥数语:“充边之事,当时有所忌讳,不敢言也,故记载甚微。”所幸,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田氏宗谱》(傅文著)最末处查到“明成祖靖难后徙浙中巨族以实边,孟昭公早虑及此,遵母陈氏太安人之命于外祖家别立户籍。永乐八年除夕,兵围一村,督田氏举族徙于陕西临洮府。幸太安人陈氏以老免。因遣义仆王老军追至苏州控告云,孟昭公已出继陈姓有户籍可凭。遂得一家复还。至今子孙繁衍,皆陈太安人与孟昭公先见之力也。然留居欢潭亦仅孟昭公一支矣。”“明靖难后诏徙浙东巨姓实边籍,田氏西徙临洮。初吾十三世祖妣陈太安人识先机,当谓子孟昭公曰:‘朝廷猜忌豪族,吾宗强,惧不免。若不早自贰,田氏墓不麦饭矣。’孟昭公乃寄籍外家,冒陈氏姓得不徙,事已归宗。”
这两段叙述,应该算是翔实、中肯、可信的。
那么,西迁临洮的田氏后裔是否真的到了目的地?迁播的路线图如何?现又族居或散落在临洮何处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一行匆匆拜别朱仙镇岳王庙,又马不停蹄,从陈留赶往临洮。
(十二)
在中国的版图上,临洮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城;在华夏的水域里,洮河也是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
但是,岳麓山下、洮水之畔文明的历史深不可测。70年前,文化大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在临洮马家窑考古中发现两所史前人类的住屋后曾断言:“中国文化发源地在洮河。”
临洮最早的方志是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的《临洮府志》,有二十六卷八册,可惜在1876年(光绪二年)已流失日本。查看《乾隆狄道州志》、《乾隆狄道州续志》得知,历史上临洮置县早于甘肃设省。公元前384年,战国时的秦献公在洮河岸边设了一个新的县置——狄道。狄道是临洮的古称。《后汉书·百官志》说:“县有蛮夷曰道。”狄道显然居住着以“狄”为主的少数民族。也从此,这个现在被称作临洮的地方历经两千三百多年设县而无变更,在中国罕有其地。
秦统一六国后,全国设三十六郡,临洮属陇西郡管辖。而甘肃设省则在元代。元代的行政区域大体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全国设十一个行中书省。公元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甘肃正式设省,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简称甘肃行省,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甘肃省的行政区域。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辖甘肃。公元1376年(明洪武九年),鉴于行中书省职权太重,废行省制,设承宣布政使。全国共设十三个布政使司,加上两京,即京师(北直隶)、南京(南直隶)共十五个行政区(简称司,俗称省),实行省、府(州)、县三级制。甘肃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临洮则设府,即陕西司或陕西省临洮府。
故,明永乐年间,“陕西临洮”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
(十三)
在临洮考察期间,我们得到了当地政协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县政协副主席陈书新、提案委员会主任赵东铭、县博物馆馆长杨顺国全程陪同,特别是事前准备充分,考虑周到,因此收获颇丰。
我们首先从洮阳古城出发,驱车往东,沿着东峪河前往窑店镇武家村。当地习惯上把县城以北叫北乡,以东就叫东乡。东峪河虽不足五十里,流域面积也集中在狭长的东峪沟,史籍里却非常地有名气。古代奇书《山海经》中已有记载,名曰“滥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之为“陇水”。秦昭王二十七年,因狄道古城在陇坻之西而得名,故称“陇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说:“陇水,今名东峪河,源出甘肃渭源县西,北流入临洮县境,注于洮水。”沿东峪河的这条不起眼的土埂石路,古代可是条官驿达道,以前官道上还有座秦皇庙,秦始皇西巡陇西郡曾歇息于此。汉唐时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必经要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发掘出汉代西征大将李仲翔的家族碑群,据考证是李唐皇朝的祖坟,也就是唐朝帝王的故里在此。东峪沟的文化底蕴之深厚可见一斑。
约莫四十分钟车程,我们来到了战国秦长城脚下的武家村村委会。听刘瑾镇长、张存德村支书、孟世忠村长介绍,武家村由渭初社、武家社、包家湾、东坪社、西坪社和田家坪等六个村民小组组成,共计322户1321人。其中田家坪社85户337人,田姓58户216人。村民收入主要以种植柴胡、党参、玉米和养殖牛羊为主。
拜访了田家坪田培龙、田永林、田永胜等田姓长者,他们一致认定祖上不是临洮人,是从外地戍边迁徙过来的。明朝初年,先祖从山西洪桐大槐树下迁到临洮北乡。清初有兄弟四人又从北乡迁至这里。后来又有一支迁到离田家坪不远的渭源县田家河乡田家河村去了。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到田家河乡调研扶贫开发工作,现在那里快成网红了。一直以来,田家河村的田姓族人仍保持着清明节来田家坪扫墓的习俗。当我们问及是否有祠堂、家谱之类物证时,他们说,田家坪有位教书匠叫田永裕,以前他家有家谱,供在祖宗牌位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它烧了。听他说过,田姓祖上是走水路到山西的。可惜他今年8月刚刚过世。专门联系了田永裕的儿子,他说老父亲生前的确不止一次说起祖上是从南方江浙一带取水路到山西洪桐,再走陆路迁移到临洮北乡的。
从窑店镇折回,我们来到了县城以北的新添镇,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北乡。临洮田姓主要聚居在该镇的两个村,一个是阴山子村田家河六社,有人口65户281人,田姓61户259人。另一个是三十墩村田家嘴社,有98户320人,田姓85户263人。
专程拜访了田家嘴社85岁田姓长者田俊礼,此人道士出身,占卜问卦营生。他说田家嘴与田家河田姓同祖同源。祖上出过不少当官的,其中有田大有、田大用兄弟俩同朝为官。查《乾隆狄道州志》,确有其人。系明嘉靖时狄道贡生,任职岳阳教谕和彰州教授。但未注明是兄弟俩。仔细查阅《乾隆狄道州志》、《乾隆狄道州续志》,发现明清两代记载的田姓官吏有田润、田济顺、田岐、田锡龄、田捷等十余人。除明初的田润外,均写为“狄道人氏”。“田润祖籍浙江山阴人,授职百户,传之润七代。”明代百户为世袭军职,统兵120人,正六品。深感遗憾的是谱师惜墨如金,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记载。
在新添镇阴山子村委会,副镇长黎华栋、联村干部赵慧琴、村支书赵世刚、村长李世民专门召集田国俊、田建军、田国佐、田国瑜等田姓长者座谈,大家众口一词,祖上不是临洮人,而是明朝初年,从山西平阳府洪桐县大槐树下强制迁徙过来的。因为戍边垦地、开疆拓土有功,列朝列代免交赋税。
的确,临洮这三个田姓聚居村落都分布在战国秦长城脚下,他们世代以屯垦、卫边、牧羊为生。虽然生活清贫、艰难,性情却依然豁达乐观、古道热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乾隆狄道州志》有“长城在州北三十五里”的记载。专家考证,临洮境内段长城比秦统一还要早半个世纪,系秦始皇他爷爷、战国后期的秦昭王拒胡而筑。因地势和防御布局,自西向东穿越今临洮县90余华里。它首起新添镇杀王坡,沿东峪沟长城坡,至窑店镇上阳山进入渭源县境内。
站在烽遂台顶,远眺,城垣障塞、蜿蜒起伏;近看,黄土夯层、秦瓦绳纹。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抚摸长城墙体的时候,分明感觉到那一层层黄土正是一页页厚重的卷帙。是远古的祖先,不,是无数代人固守家园的见证。
(十四)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鹞窝。”
据《山西移民史》(安介生著)和《洪桐县志》分析,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元末明初的战乱基本没有祸及,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中原地区稠密,而地处晋南的洪桐又是当时山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户均在10人以上。但山西土地少,“地狭人稠生计难”的矛盾突出。明朝时在洪桐县城往北二华里的官道边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设有规模很大的驿站,还有一棵“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枝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正是综合考量了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诸多有利因素,于是在洪桐县的广济寺设局驻员,为被迁之民集中办理迁移手续。广济寺是明初大移民全国最大的派遣站和点行地。大槐树老鹞窝下就成了来自山西及江浙一带涉及800余个姓氏的众多迁民的集聚之所。迁民们在这里登记造册,统一领取衣服、路费、耕牛和种子等供需物资,官府甚至承诺免赋税三年。然后按官府指定的线路、方向、地点,在官兵的监护下编队列伍,分别迁往异乡。仅永乐年间,官府就在广济寺集中办理全国移民达八批次之多,百万人之众。临洮田氏一支始祖就是明初永乐年间自山西平阳府洪桐县大槐树下迁居陕西临洮府北乡。而大槐树的故事,天长日久,口耳相传,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广为流传。成为远走他乡的迁民们留恋故土的又一个标志,寄托乡愁的最后记忆,也是永恒的记忆!
无独有偶,与大槐树的故事如出一辙的还有地处江南繁华之地的苏州阊门城楼的传说。
(十五)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羁旅诗脍炙人口,名流千古。然而,对于明初大迁徙的广大江浙迁民来说,这里并非是诗情画意的浪漫之处,而是离乡背井的伤心之地。充塞的是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的愁眠。
据《大清苏州志》载,寒山寺初建于梁代,唐代诗僧寒山曾住于此而得名。寒山寺旁有两座桥,“江村桥”和“枫桥”。枫桥在唐以前名封桥,因河边有经霜叶红树之故,加上吴语封、枫同音,张诗以枫误作封,自此而改名枫桥。阊门在苏州城的西北,自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在此相土尝水建筑阖阊大城以来,阊门就是苏州城的主要城门。出阊门西行就达枫桥和寒山寺。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江南段后,京杭大运河就从枫桥和寒山寺旁穿过,经阊门码头抵达苏州城。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又是浙东运河的起点。过钱塘江还可达浙南、浙西乃至闽、赣等地。苏州处在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是运河上南来北往的水路要冲。明初,迁往苏北、中原、京城及边疆地区的杭、嘉、湖、苏、锡、常、镇、松等地的广大迁民要过江,所以必须走水路。出阊门、入大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最经济、最便捷、最理想的路线。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南巡走的也是这条路。《吴郡志》记有宋代时谚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红楼梦》里称之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由苏杭所处的交通要道、水路要冲、货运集散地、人口聚居区等区位优势决定的。
据《中国移民史》(葛剑雄著)和《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吴必虎著)分析,明初如此大规模的官方强制性人口迁徙,组织者势必要集中被迁之民登记造册,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会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旧时寺庙古刹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外,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有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广大江浙地区的迁民。阊门一带也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出发、集散之地。巍峨的阊门城楼和声名远播的寒山寺成了迁民们惜别江南的最后一站,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至今,许多苏北人称自己的祖先是苏州阊门人,这种文化现象与大多数中原人所说的祖籍是洪桐大槐树下是相同的。
1410年(明永乐八年)除夕,官府兵围欢潭,强迫田氏巨姓西迁陕西临洮府,凡有不从者,就地处死。他们在官兵的解押下,扶老携幼、离家舍业,渡过暗潮涌动的钱塘江,沿京杭大运河江南段,走水路从杭州至苏州。也许是人口众多、行动迟缓,或许是寒山寺办理移民手续费时耽搁,休整时间稍久,从而给因年老免于充边的陈氏太安人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取得其儿孟昭公出继陈姓的户籍证明后,火速派义仆王老军追至苏州控告官府,才使孟昭公一家得以复还。
然而,绝大多数田氏族人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在办完迁移手续后落寞离去,在灯影桨声里再度登舟北上,出阊门、入长江、至镇江。又经瓜州到淮安的里运河。淮安是京杭大运河联结淮河水系的重要枢纽。要到达山西平阳府洪桐县有两种走法:一是入隋朝大运河,经淮河至通济渠到开封、洛阳;另一条是沿元朝大运河继续北上,经淮安到台儿庄的中运河,台儿庄到临清的鲁运河。运载迁民的舟船最后停泊在洛阳或临清。迁徙的队伍弃舟从车或以步代车,从陆路到达设在洪桐县广济寺的全国移民机构。稍作停留,又从大槐树下启程,赶往荒芜陌生的临洮北乡。因其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备受艰辛,更加增添了迁徙的悲壮色彩。这就是明永乐年间欢潭田氏的西迁之路。
、 (十六)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山西洪桐大槐树、苏州阊门城楼只是历史上移民的代名词,但明初官府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进行的大规模、有计划、强制性的迁民运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乡恋土是人之常情。中国又是个传统的农耕社会,要农民尤其是江浙一带富庶之地族聚而居的乡民强行离开自己的家园田舍、迁居异地,自然心生不愿,甚至怨愤。明清时期文字狱盛行,史家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地方志乃至族谱、家乘不见或鲜有记载的真实原因。毋庸置疑的是,通过明初人口大迁移,客观上有利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大融合。
辞别临洮之际,登临岳麓山巅蜀汉姜维点将台,塞上之秋,天高云淡,极目远望,只见那股流经东峪沟、《山海经》中称作滥水的涓涓细流汇于波光粼粼、千年不息的洮河后,似一条蛟龙,穿越洮阳古城,自南向北注入咆哮的黄河。然后一路向东,奔流大海。
想起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那首散文诗,“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湖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这不正是一个江南乡村望族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