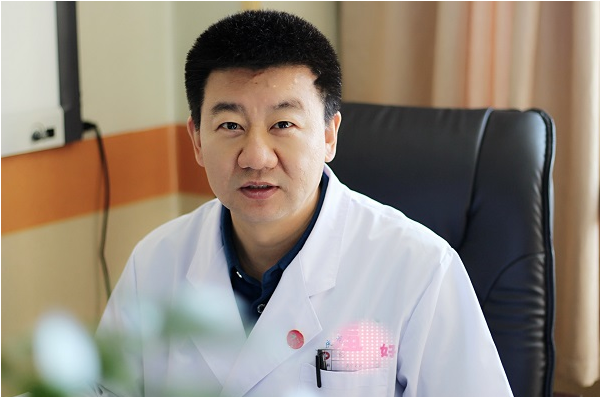燕兆林:乡席
我在这里说的乡席是指乡村里的宴席,也叫“酒席”。有许多人出席,常常为纪念某事而举行的酒席。过去在乡下,大凡有出嫁女子、娶媳妇、老人辞世(埋坟、白期、三周年祭日)红白喜事、修房垒屋、乔建新居等重要事情,就得请乡下的先生翻黄历,掐八字,算时辰,选择黄道吉日,大办宴席(酒席)来款待四路亲朋好友和和左邻右舍的庄村伙子。而在这里特指婚宴,也称“吃喜酒”,是婚礼当天答谢宾客举办的婚庆筵席。我国民间早就有“无宴不成婚,无酒不嫁女”之说法。如今,在城乡逢年过节,尤其是每年阳历的元旦、五一、国庆,农历的正月十五、二月二、八月十五,是城乡青年男女结婚旺季,节前十余天,请帖犹如雪片飞舞。今年五一假期前夕的一天,我竟欣喜地先接到了一个口头电话请贴,是一个小山村的村支书的。后来就收获了一页很精致美观的“雪片”,是来自康南山区俗称六十里火烧河沟里偏远山村一位村支书的喜酒之请。20年前我曾在那个小山村驻村时,与他一起共事相处三年多,今天给他孙子娶媳妇。这些年,我收到来自康南、康中、康北及县城飞舞的“雪片”多如牛毛,有的是县城来的,有的是乡下农村来的;有的是中学同学的,有的是在乡村工作这么多年一起共事相处过的同事的,有的是新近几年喜爱上写写画画的文朋诗友的,有的是从事各种生意朋友的。如果路途较远,有便车就亲临光顾去凑个摊子,给主人家一个体面;反之,就打个电话或让同事捎带搭个礼,并通过电话或叮咛同事向主人诚恳叙说未赴的缘由,征得主人家的凉解。宴席有时在县城,有时候在乡下山村,一般的请帖大多只是去搭个礼不坐席,唯独是老同学、老朋友、老领导务必亲临光顾。但这次却一反常规,大驾光临。尽管前夜下起一场大雨,路远泥泞,我通过电话了解通往乡下的路况,决意如期前往,一来看望一下当年共事过的人手,二来再体验一下别具一格的山乡婚宴。
早晨起床,披衣而出,天气放晴。乘上去县城的小汽车,直奔公共汽车站。班车从县城出发,我无意欣赏车窗外如画的景色,脑海屏幕上尽是当年乡席的画面。20多年前的秋天,结束长达15年的学生生活,有幸参加县上农村返乡高中毕业生招干考试,我被招聘分配到远离县城40多公里的乡下,先后当税收人员和驻村干部,大山深处22年的农村生活,让我一次次地亲历见证乡席的变化。那是90年的秋冬季节,正值农村税费收缴的高峰期,在那税费任务收缴喊得山响的年代,尽管当时乡席被当成“陈规陋习”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的禁令仍禁锢着村民大脑,但山民们依然固守着千百年来传承的乡俗,无论是红白喜事,都兴办酒席。当年的乡席,无不打上时代烙印,成了一个地方贫穷落后的缩影和诠释。
乡席,在县境内各有千秋,南、中、北三大地域乡村不尽相同,按照各处风情民俗和传统及当时家庭经济状况而办置酒席,席桌是四方形的八仙桌,有大小之分,四条木制油漆的长凳子,一面座三人就是十二人席,上下座2人,左右座3人就是十人席,一面做2人就是八人席,乡下人都统称为“十大碗”。婚宴菜肴数目为双数,通常以八个菜象征发财,以十个菜象征十全十美,以十二个菜象征月月幸福。那个年代里,国家对农村实行交售生猪任务的政策规定,每年一个村里都要给国家交售十几头生猪的指标,平均每三、四户农家交售一头,农家大多喂养的猪都上交任务了。平常时日就没有猪肉吃,只能办成简单的素席。先是上四个干蝶子,后上四个热菜,有黄瓜、白菜、萝卜、豆芽、洋芋、凉粉等菜,最后再上“十大碗”:两碗豆腐块、两碗豆腐片、两碗油炸面疙瘩、一碗海带、一碗粉丝、一碗洋芋片、外加一个大腕,装着各种素菜的大杂烩。在那年代里,一个山村里谁要是挣死拼命地多喂养一头猪,耍个牌子,讲个排场,办成荤席“十大碗”,就好像是放了颗卫星。说是荤席,其实名不符实,实为半荤半素,即素席“十大碗”减成两碗。增添一碗肥肉片,一碗肉砣罢了。乡席的主食,一般是清一色的白面馍。说是白面馍,其实假冒产品,一半是白面,一半是白包谷面。乡席上从来不见米饭,当地也不产大米,偶尔从山外面捎带点回来尝个新,乡下人两斤包谷面换外面人的一斤大米,也就是乡下人与城里人用自产的包谷面兑换大米吃,一户人顶多换三五斤,逢年过节吃一顿,大半都是在过新年吃一顿,权当过一下米饭瘾。乡席上的酒,有瓶装酒,有自制的二脑壳酒,有购买酒厂的散包谷酒,在康北有麦曲酒,在康中有黄酒。当年的乡席,如今不值一谈,甚至寒碜至极。然而那个年代,对于常年生活在偏僻边远的大山深处的乡民们来说,一年忙忙碌碌,风雨兼程,艰难拼搏,到头仍是吃着粗茶淡饭,想吃顿乡席成了乡下人盼星星盼月亮的事。
那时候,大凡吃酒席的人,礼节比较轻且很随意,搭礼大多是包谷,也有麦子,一般人家搭一升,亲房伙内搭两升,顶亲的弟兄姐妹搭三升。也有搭钱的,搭礼者也会算账,包谷换算成钱,一升包谷值一元钱。该搭一升包谷的,怕麻烦,就不搭包谷,空手子去搭一元钱,也有搭五角钱的,亲房伙内的搭两元钱,顶亲的弟兄姐妹搭三元钱。最高的礼是“挂红”,山外商店(当时是供销社分店)里扯六尺布,一尺布四角钱,六尺布两元多钱,再加上六尺布票的价格,总加值不超过三元。“挂红”的大多是亲房伙内和顶亲的弟兄姐妹,“红”字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往事主家院落绳上一搭,搭礼者体面风光极了,往往被尊管视为贵客,安排座位上席。
那年代,农家置办酒席没有多余的家什,比如桌凳和锅碗、筷子,酒杯等,办席的事主家得早早地挨家挨户地借,十天半月前就得在房前屋后垒灶,请庄村伙子背些柴火备用。“十大碗”的乡席,对贫困的农家人太有吸引力了,那怕雄关漫道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只要事主家捎个口信,也要来赶席,还未到主人家已是垂涎三尺。当年长有威望、声音洪亮、嗓音高的总管一声“开席”令下,话音未落,男女老少坐席者如同冲锋陷阵一拥而上,抢着坐头一轮席,一是想早点一饱口福,二是想早点坐完回家干农活。乡席一次只能开两三桌,顶多开四五桌,从朝霞满天一直持续到星月当空。一桌十二人,小方桌,长条凳子,或是草墩子。一桌席刚拉开序幕,每人身后早已站着一个下一轮子坐席的人,犹如站岗放哨的兵娃子,令席桌上的人横顺不舒服。每道菜刚端上桌,十二双筷子便发起总攻,眨眼功夫便一干二净。席桌无一例外地摆在敞坝院里,有时正吃得兴起,一阵大风刮来,顿时饭菜上尘埃落定。坐席者拿管这些,连土杂物一起狼吞虎咽咽进肚里,一轮席,风扫残云一般,二十分钟便结束了战斗。待最后一口菜汤咽进肚里,坐席者身子还未离席,身后人的腿早已插了进来,农村人管叫“插腿席”。
俗话说,吃不了兜着走。当年乡下人吃酒席却是舍不得吃兜着走。大人坐席,舍不得吃独食,总要将席桌上干碟子里的果子之类夹在一边,用腰包或裤包随身带的小手巾包好,装进衣服的兜里带些回家,给望眼欲穿的孩子一个惊喜,或让足不出户的老人尝一口。而“十大碗”中的肥肉片、豆腐片、面疙瘩和馍,均成了“兜”的对象。每桌一碗肥肉片,不多不少十二片,十二个人每人一片,谁也不会多吃多站,谁也不会拱手相让,豆腐片也是每碗一人一片,面疙瘩也是这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馍上,放一片肥肉、一片豆腐、一两个面疙瘩,顺手折一截树枝,插在这一摞东西上面,串成一座“宝塔”,坐席人手捧着“宝塔”回家,惹得狗流出青口水紧随其后。也有人从家里走时,便揣上剥包谷棒子时剥下来的包谷叶子,包上属于自己的肉片、豆腐、面疙瘩,带给家里的孩子。几乎每个坐席者,都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你拿我也拿,谁也不笑话谁。反而个别空手而归的人,回家后招致而来的是“吃独食的饿死鬼”之类话的一顿臭骂。
从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在康南乡村,二十多年来,我一次次的参加乡席,一幕幕情景至今难忘。记得一次在一个毛包山的小山村,一位儿子怀揣一片爱心,自己舍不得去乡席上解馋,让年迈的老母亲去吃一嘴。老人拄着拐杖来了,看到桌上的“十大碗”,好多没见过这样的美味佳肴,脸上笑成了一朵花,用颤抖的手,好不容易夹起一片肥肉放进嘴里,也许过于兴奋激动,一口气没上来,活活地噎死了。老人鼓着眼睛,半截肉在嘴里,半截肉在嘴外,到死没有把一片朝思暮想的肥肉咽进肚里,死不瞑目啊…….一位中年妇女,丈夫去世后,含辛茹苦拉扯两个孩子。一次,她吃完酒席,手捧“宝塔”回家,心里打着“小九九”:两个肉片、两个豆腐片、两个面疙瘩、一个馍,够两个孩子吃个半饱。正当她走过一道山梁快到家门口,心里美滋滋的,殊不知大祸从天而降。一只饥饿年代的饥饿乌鸦,像疯狂的强盗一样,不知从哪儿冲下来,蛮不讲理地夺走了她手中的“宝塔”,箭一般地飞上那边的山林。中年妇女的美梦破灭了。嚎啕大哭:“老天爷呀!我的命咋这样苦啊!”刚哭了两声,嘎然而止,原来乌鸦叼起的“宝塔”解体了,那个馍从天上掉了下来,像一片树叶飘落山涧。中年妇女想完璧归赵,手抓茅草,顺陡崤的悬崖而下,想在万丈深渊里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回那块馍。她下去了,却再也没有上来…….那一夜,两个孩子的泪水打湿了山村……。
乡席,成了村落里狗的乐园。只要村落里有一家办酒席,村庄里的狗闻风就来,它们大摇大摆地从四面八方窜过来,也想与吃酒席的客人一同凑个欢欢。村落里有白、黄、黑、花这四种颜色的狗,来回在事主家方园四处转游,寻机捕猎遗留在地上的饭菜。有的狗乖间、机灵、听话,卧在一旁耐心等待主人家的唤使,见有客人光临会摇着尾巴打招呼,显得很亲热。而有的狗则显得狂妄、滑稽、不安分守己,四处乱窜,见有客人来还“咣咣”地乱咬。不时,一见厨房有人出来就紧跟过去,看看有没有给他倒下饭菜饱餐一顿。一会儿溜进厨房寻机食物,挡脚挡路的,惹得灶房里的女人和男人怨气载道,用木棒追赶出去,一会儿又在席桌底下横卧等待观望,指望坐席者扔下骨头或夹不稳掉下来的肉菜,美美吃一嘴。有个古典“二龙抢宝”,就是对乡席坐席者与席桌下狗抢吃活的最好诠释。一位坐席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夹了一块肥肉,刚夹在筷子上,听着坐席者在天南地北的谈闲聊天,谝的日月忘光,不慎捏筷子的手一晃到口的肥肉就滑落掉到席桌下面,早已如饥似渴的狗吞吃了,而另一条还没等着饭菜的狗闻风而来,同抢那片肥肉,致使两条狗相争打架,以至咬伤坐席的客人,咬的轻点的,大腿上伤点皮留下痕迹,也有咬破裤子的,给事主家添加乱子。
峰回路转处,一阵霹雳叭啦的鞭炮声,一曲喜庆愉悦的歌声,一阵喇叭声打断了那些不坎回首的往事。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乡席,该是啥样子?
迎着炙烤的午阳,我被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载进了小山村。这是一个八、九十户人家的深山村落,“5.12”地震中村民们失去了家园,灾后重建中家家建起了新房,沿河边而建的清一色的砖混结构楼房错落有致排列着。晨阳和夕阳照耀着小山村,给每一座房屋都涂上阳光的油彩。听说自“5.1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以来,村里已有80余户人家在封顶时,酒席办的一家比一家丰盛,也有四、五户人家在新房里给儿子或女子娶媳妇(出嫁),酒席也办的一家比一家排场。走进事主家门前,只见门楣上贴着“志同道合成夫妇,谊重情深结姻缘”和“喜酒杯杯喜事喜逢喜日子,新风处处新人新建新家庭”等四幅鲜红的婚嫁对联,在午阳的照射下亮丽耀眼。
我和当年在这个乡担任书记的刘忠奎及电管站的李如峰被村支书捧为座上宾,交谈间接亲的队伍进村了。再也不见当年用马或骡子娶亲的场面,村村通了公路,乡下人接亲和城里一样用上了小汽车。接亲的六辆小桥车在村头还未停稳,四十响礼花响彻云空,霹雳啪啪的鞭炮声沸腾了山村。新郎和新娘手挽着手,从披红彩的“桑塔纳”里走了出来。新郎----我同事的孙子,听庄里人介绍小伙子很能干、很聪明。在外求学回来跟爷爷做了几年农副土特产生意,加之人缘好,机遇到,被县上某单位招聘为工作人员,收入不错。
总管一声“各位亲朋好友,四路亲戚,坐席了”,头一轮就开了十桌。我和刘书记和电管站的李站长自然被安排坐了头轮席,席桌上再也不见昔日的“十大腕”,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乡席。酒菜也很丰盛肉有排骨汤、粉蒸肉、扣肉,肉块切得又大又肥,另有木耳、香菇、竹笋等。六个凉菜先闪亮登场,紧接着六个热菜争先空后报道,接下来鱼、鸡、银耳汤之类也纷纷亮相。也记不清端饭的执席者端上了多少碗、多少盘,席桌上摆的满满当当,菜的数量和档次,丝毫不亚于县城里,烟酒的档次也不低。再也不见当年的风扫残云、狼吞虎咽,坐席者慢慢品尝菜肴的味道,边聊边尝,有的菜吃了不到一半就下课了,有的菜连筷子都没动就被扯走了,被后来端上的菜取而代之。最后是主食米饭,外加几个下饭菜。席间,会猜拳的猜拳,不会猜拳的蚕鸡儿或石子、剪子布,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山乡宴席。
趁席还没结束,人还清醒,我去搭个礼,搭一百元吧,在如今的乡下也算大礼了。谁知瞅了一下礼簿差点啥了眼,一百元成了小不点。礼簿上最小的数字是五十元、一百元、,也有二百元、四百元、六百元的,还有一位竟写了礼一千二百元,也许前面几页还有更高的。
再也不是“插腿席”,身后再也没有“兵娃子”。那些暂时没有座上席的人,在各处转悠和聊天,等下一轮,有的谈天说地,有的参观新居,有的年轻人在主人房间里玩扑克打游戏,有的则在庭院里唱歌曲。有的唱《感恩的心》,有的唱《走进新时代》,有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哪是谁家的光盘里演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奔波、奋斗,我们为她幸福,为她挣光……”
歌声在小山村飘荡,歌声抒发着山乡农民的心声。
那一刻,我的内心发出深情的感叹: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个山,梁也还是那道梁。今天的山乡再也不常昨日的歌谣,山乡变了样,变得越来越富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