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福田:七律 咏鲁迅
七律 咏鲁迅
一因诗力羡摩罗,
便做新华锦上梭。
为解胞民离水火,
敢凭只楫试江河。
平人唤起难阿Q,
西语移来重彼俄。
慈母心轻天下事,
从他祝福共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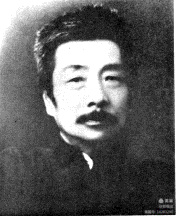
注:
鲁迅先生十八岁入矿务学校,迨至学校解散,乃赴日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历时二年,因思想变化,乃弃医学学籍,到东京,与友人提倡新文艺。
鲁迅先生在当时文坛,杰出特立,皎皎然与众不同。他蓝衫囚发,犹如辛勤园丁,左右剪伐栽培,比之狂者狷者,上下探寻求索,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为了改创造中国人之思想,为了去除旧的劣根性,建设新的国民性,为了“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辛苦万端,如梭织锦。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药,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张定璜说鲁迅先生:“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先生一生事业,端为唤起民众。他以往事说现实,从而预言未来,他认为唤起平民是重要的,他的事业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旧中国的人们,灵魂上负载数千年传统之重担,旧中国的传统,其表现可憎,其结果可怜,然而,时下不能不承认其存在,又不能不催人因此反省自我灵魂究竟是否完全脱却数千年之传统阴影。这应该是《呐喊》、《彷徨》的伟大处之一面。而这一面,过去是习见的,不以为奇的。
许广平概括说:“翻译和介绍苏联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在鲁迅毕生的革命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据粗略的统计:在他将近600万字的著作中,苏联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就有160多万字的数量,约占他全部著作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全部翻译量的一半以上)。”
据记载,鲁迅先生之母,喜欢读长篇小说,旧小说阅览几尽,亦甚喜新小说之《广陵潮》,杂志中之《红玫瑰》等。有一天,,她对鲁迅说:“人家都说你底《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待其读后,又对鲁迅说:“我看也没有什么!”这记载平常淡朴,亲切自然,很有意思。
鲁迅之探讨精神令人钦敬,鲁迅之思想光芒不可掩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