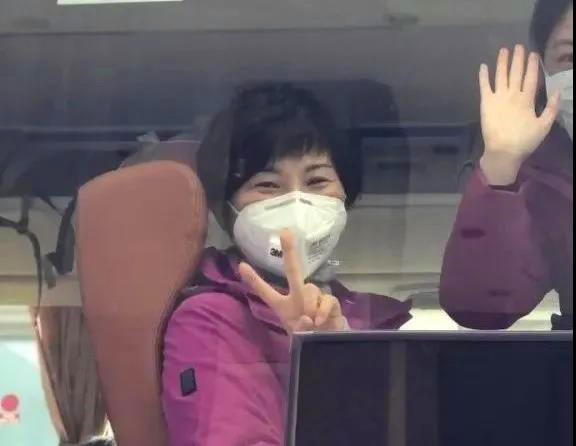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与欧洲危机
作者简介:林德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目前欧洲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民粹主义的挑战,而忽视了导致目前欧洲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即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本文着重讨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政治渗透及其政治影响。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渗透是以渐进形式实现的,是在欧洲主流政党的共同助推下,借助于应对危机的改革和欧洲一体化的建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透到了欧洲政治中。抵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分化和碎片化便利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新自由主义对欧洲社会的失衡、欧洲的民主制度侵蚀以及社会关系的极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欲走出危机,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上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关 键 词: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欧洲危机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在欧洲一度受到普遍声讨,但危机的形式变化改变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如人们所预言的死亡,反而在以新的制度化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此,欧洲的主流政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面对欧洲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欧洲主流社会在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民粹主义的挑战时,依然不愿意触及新自由主义政治这一更深层的问题。但欧洲欲走出危机,矫正失衡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上反思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影响。
近年来,欧洲的危机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的趋势,它在凸显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引发危机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即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渗透和制度化影响。伴随新自由主义渗透的欧洲政治生态变化和社会关系失衡是导致目前欧洲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欧洲欲真正走出危机,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政治的遗患。
一 欧洲危机的形势变化及其政治意义
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开始在欧洲蔓延以来,欧洲危机的形势几经变化,从最初的金融或经济危机逐渐向社会和政治危机演化。在此过程中,矛盾的焦点问题以及人们对危机的理解认识都在改变,围绕危机问题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形势也日益复杂。
危机之初,欧洲的主流社会往往将这场危机视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放松控制政策的恶果。新自由主义由此成为舆论讨伐的主要目标。欧洲主流政党纷纷表态,以示自己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界限,并呼吁加强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英国工党首相布朗都表示要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布朗宣称拒绝“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信条”。媒体也称危机恰恰证明了欧洲模式的正确,如荷兰报纸洋洋自得地表示“欧洲资本主义更适合于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挑战”。①学术界也加入了对“后危机时代”政治话语的讨论。
但随后欧洲危机的实际进程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脱离了这一轨迹。危机的加深,尤其是欧盟一些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问题的暴露,显示危机并不仅仅只是一场美国式金融危机,而是与欧元以及欧盟体系密切相关的欧洲经济危机。可面对这种形势,主流政党的政策选择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得人心,围绕危机问题的欧洲社会分化开始凸显。对于主流政党来说,援救大银行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援救出现主权债务问题的国家以避免欧元体系的崩溃并稳定欧盟,这些似乎都是无可选择的。为此所必须实行的紧缩政策,实际上成为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助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先决条件。而紧缩事实上是以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也就是说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导致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强烈不满,而紧缩政策和欧盟救助问题则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此问题上,主流政党事实上默认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而进步的左翼力量则高举了反紧缩大旗,并将紧缩政策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摧毁欧洲”;②但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则利用民众的不满,将矛头指向了欧盟和移民问题。
此后,在经济危机持续、民众的不满情绪积累的背景之下,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在欧洲蔓延,并挑战了欧洲既有的政治传统和秩序,而欧盟问题、移民问题以及2015年之后的难民问题成为不同力量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民粹主义对欧洲既有政治秩序的挑战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在国家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对既有的传统左右主流政党结构的挑战。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在国内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南欧一些国家的新激进左翼的崛起,从不同方向挑战了既有的传统政党结构和主流政党的地位;在欧盟层面,民粹主义凸显的疑欧和反欧立场以及所诉诸的简单化的解决问题方式(如全民公投)直接影响了各国的欧洲政策,威胁到了欧盟的生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欧盟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称民粹主义是“对欧洲最大的威胁”。③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意大利的宪法改革公投同样引发了人们对欧洲政治新的不确定性的极大担忧。其实,除对欧洲既有政治结构的冲击外,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蔓延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从思想观念上对西方普遍的民主原则的侵蚀。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诉诸的精英与人民的对立,④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式所诉诸的非理性的方式,⑤以及它本质上所体现的反多元主义性质,都从深层次挑战了西方既有的民主政治文化。⑥
民粹主义对欧盟、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突出,但不能把这些问题或把民粹主义本身理解为导致目前欧洲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根源。一则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二则从逻辑上讲,危机的环境才是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繁衍的真正土壤。实际上,声称存在严重的(政治、文化或经济)危机,这是不同类别的民粹主义的一个共同的思想特质。⑦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兴盛依托于大众普遍的危机意识。欧洲大众在欧盟、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忧虑,实质上是他们对失去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危机感的一种反映。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威胁。而欧盟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在于它是一个缩影,近乎于欧洲传统社会发展模式被侵蚀的过程的倒影。因此,民众的疑欧和反欧态度实际上是对由主流政党所主导的欧盟模式的一种否定。而这些问题,都要追溯到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政治渗透,尤其是其制度化影响。
二 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渗透
英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发端地之一,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曾是新右派经典的政治宣言。但这种新右派政治带有显著的盎格鲁特色,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其他地方,典型的新右派政治还并不具有主导地位。欧洲传统的社会特征依然明显。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对新自由主义也还抱着较强烈的抵制态度。不过,借助于新右派的政治氛围,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的核心要素即市场中心观念在逐步渗入欧洲其他国家、其他政治力量,甚至是一些表面激烈抵制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左翼力量。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首先涉及新自由主义概念不同维度的理解。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有三张不同的“面孔”:作为一种智识,它主要表达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套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政策体系,它包括了一些以自由化、放松控制、私有化、去政治化和货币主义等为特征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它表达了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逻辑,其中包括了一套对合理政治秩序的理解。⑧三者交互作用但意义并不等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往往先是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思想,然后转向成为一种完全膨胀的政治合理性,据此,所有的人类生活都从属于市场准则。⑨后者即上升到了一种政治方式。
与此一致,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政治渗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它是以确立市场观念的合理性为突破,从多方面推进的,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进程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政治渗透至关重要。
首先,在欧洲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左翼政治方式出现问题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理论为其赢得了政治合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调控资本主义模式危机,以及进步主义力量缺少相应的替代性理论和政策方式,皆是新自由主义确立其思想“合理性”的客观前提。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流行时产生并诞生于对它的批判,但兴盛于后者陷入困境之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欧洲传统社会福利体制的持续性危机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有关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解释。长期以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的平衡这一假设基础之上。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增长之间不可能取得平衡。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在思想和政策方面都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其攻击的目标是政府控制。在进步主义领域缺少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性理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方式被当做矫正大政府弊端、克服通货膨胀问题的政策手段来运用。此外,作为其核心的市场竞争逻辑也被认为更适应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竞争加剧的现实。
其次,欧洲的主流政党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权得以实现的共同推进者。
欧洲左翼往往把新自由主义政治与新右派关联。其实,在欧洲大多数地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更多是在应对传统体制危机的改革过程中,从观念改变到制度化,逐步实现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需要和国内政治及改革的压力,执政的主流政党(不论来自左还是右)自觉和不自觉地通过向市场妥协的方式进行改革,以市场为主要手段的改革逻辑逐步渗入了主流政党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议程中。而这种改革,既来自保守右翼,也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如80年代后瑞典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主要是由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引入的。密特朗成为法国首位社会党总统后,很快就放弃了其社会主义的改革计划,转而接受市场经济。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以维姆·科克为领袖的荷兰工党。虽然这些改革最初主要是为了应对危机或变化的环境而非刻意迎合新自由主义,但在无形中将市场的观念置入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意识中,并使后者认可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如英国工党1997年重新执政后的首个政策是将货币决策权交给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在此基础上,90年代中期后的“第三条道路”明确将灵活的市场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议程的主要内容。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英国新工党事实上认可了撒切尔政府改革的基本框架,包括其限制工会的政策。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政府推进的市场化改革程度甚至超过了此前的保守政府,尤其是其《2010议程》大大推进了以市场化改革德国劳动市场的进程,并为此后的默克尔政府铺平了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进程所表现出的失衡——即坚定的市场路线与缺乏实质内容的社会观念和政策,意味着它实际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总之,强化市场机制同时却弱化欧洲传统的社会机制是在欧洲主流政党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再次,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成为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欧洲被制度化的一个有力路径。
20世纪80年代后正是欧洲一体化改革加速的时期,欧共体迅速发展为欧盟,欧元体系顺利诞生。对于欧洲的主流政党来说,一体化承载了欧洲应对共同危机、全球化挑战以及冷战后欧洲战略地位变化的挑战等众多政治目标,欧盟是主流政党共同努力的结果,维持欧盟的稳定与发展也是其基本共识。但在一些理念上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欧共体最初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国际自由贸易与国内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妥协,因此也被称作欧洲版的“嵌入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⑩但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单一市场的启动,统一大市场成了目标本身,社会政策目标反而成为一种“壁垒”。欧洲一体化从“嵌入自由主义”转向了“嵌入新自由主义”(embedded neoliberalism)。(11)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合法地置入欧盟的结构之中,如鼓励竞争、限制国家对商品和服务的保护。在有些领域,如电信和高速铁路以及在整个服务部门,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法律指导,欧盟直接推动了自由化的进程。在货币政策方面,“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只是关注防止通货膨胀,却不关注增长和就业。由欧盟的权力机构组织进行的谈判也使得欧洲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受到了自由化的约束。此外,通过欧盟的司法制度,经济制度开始侵蚀社会安排,致使后者与前者分离,该体制最初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改变。“欧盟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得以在欧洲制度化的渠道。”(12)
欧盟的一些制度安排受到了企业家组织的特殊影响。本来,对于欧洲的区域主义联合存在三种不同的观念:新自由主义、新商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其中,新商业主义寻求通过各种方式(征服外部市场或地方保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市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则希望在新商业主义的保护旗帜下,有机会提供一种“社会欧洲模式”,以抵制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潜在破坏。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影响可成为一种区域主义的替代模式。这就是撒切尔警告过的“德洛尔支持的社会主义”。但这种观念未能实现,因为在内部障碍清除的同时,外部壁垒并没有建立起来,内部市场也为外来者提供了同样的机会。最初把一体化当做“欧洲捍卫者”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被放弃了。大资本的游说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table of Industrialists,ERT)的游说助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但这些公司本身全球化程度更高,它们同样希望扩张外部市场,因而对于“欧洲捍卫者”的观念并不感兴趣。而欧洲的区域治理大多是追随资本的领导。(13)
通过上述进程,在欧洲各国的国内改革、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以及应对2008年后的欧洲危机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别无选择”的思维定式不断地左右着实际的政策选择。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已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入欧洲的国内政治和欧盟制度。
三 反新自由主义力量和运动的碎片化
欧洲有重视社会观念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强大的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基础,这些都本应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但面对欧洲自身的危机,抵制新自由主义力量和运动的碎片化限制了其实际效果,同时也削弱了欧洲左翼重塑欧洲政治的能力。
(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分化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点,即它所针对凯恩斯主义、国家统治主义(statist)以及福利主义的,首先是对社会民主政治的打击。所以,作为欧洲传统左翼政治主要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思想和政治空间。
但从一开始,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试图抵制新自由主义政治时即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试图抵制来势汹汹的新自由主义,但另一方面,它需要面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模式陷入困境的难题。也就是说,抵制新自由主义政治是与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同时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化首先也因此而起。面对欧洲的危机和资本力量的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本能政治反应是进一步向左后退,如英国工党在福特领导时期(1980-1983年)受托尼·本的极左力量影响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纲领,密特朗上任之初推行的社会主义计划,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施行的由工会提出的雇员投资基金计划等。但这种“左倾”反而使党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由此出现了一种反向的变化,即上述社会民主党向市场妥协的趋向,而且它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政治趋向。这种趋向本是受实用主义原则驱使的,但当社会民主党人试图进一步把这种趋向转化为对传统左翼政治的明确放弃(如“第三条道路”所示)时,它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以及其支持力量的进一步分化。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分化也削弱了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抵制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能力,这尤其反映在欧盟问题上。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显然未能利用可能的形势,推进欧洲社会政策目标的制度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货币联盟建设的关键时期,欧盟15国中有13国由左翼领导或参与执政,左翼却未能利用这种形势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输入欧盟的制度中。欧盟左翼内部巨大的分歧阻止了这种发展。当时若斯潘攻击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威胁到了欧洲一体化,并要求欧洲货币联盟社会民主化,但布莱尔强烈反对在欧洲层面上的这种干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后来围绕欧洲未来的讨论中。当时相当一部分左翼要求将“社会欧洲”制度化,包括建立真正联邦化的社会政策,并在理事会中扩大特定多数投票(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QMV)制度,但被一个右翼联盟阻止,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都加入了这个联盟。而欧盟的制度一经确立后,新自由主义的观念主张已经通过制度化方式反映在欧盟的机制中,社会民主党的主体进一步被该制度绑架,转而要去维护它的一些体现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政策。这也正是2008年危机开始后,本来信誓旦旦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二)激进左翼思想和政治运动的碎片化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上述变化,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激进左翼事实上扛起了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它们所支持的一些社会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影响,如欧洲宪法在一些国家被全民公投否决,2008年金融危机后声势浩大的反紧缩抗议运动等。但激进左翼在欧洲既有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限制以及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本身的碎片化导致其实际的政治效果有限。
首先,这支队伍构成复杂,而且在冷战结束和传统左翼政治的信誉下降的背景下,激进左翼一度陷入一个历史的低谷。作为传统欧洲共产主义最大力量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或解体,或急剧衰落。许多传统的共产党组织也开始转型。进入新世纪后,一些激进左翼才显示出止住下滑的趋势。其次,激进左翼反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虽然明确,但其立场更多属于防御性质。欧洲激进左翼反对欧盟既有的结构和政策,如它们反对欧洲宪法是担心在“自由和不扭曲的竞争”条款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被合法地置入欧盟的结构中,担心欧盟会威胁到国家的权力。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政策本身。再次,激进左翼中一些极左力量与温和力量之间的冲突也导致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内耗。如一些托派组织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并把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所有改良行为都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因而在国内以及在欧盟的许多政策问题上其立场既针对右派也针对其他左派。
总之,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赢得霸权不是因为跨国集团的一致组织,而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一个碎片化的反对力量。(14)
(三)进步主义理论的碎片化
在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运动中,进步力量在思想理论方面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少替代性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进步主义力量抵制新自由主义和重塑未来政治的能力。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反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塑是并行的。在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失去信誉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在努力探索对未来社会民主主义新的系统化解释。其中有两次大范围的讨论,即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讨论和2008年后围绕“美好社会”的讨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了这两次讨论,但结果都不理想。“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倡导者们试图发展一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和政治议程,尤其是将灵活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民主主义新的社会观念相结合。但该理论缺少一种像过去的凯恩斯主义那样将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手段,因而其实践——如作为其政策手段的灵活的市场机制、疏远工会、通过工作福利(workfare)机制改革福利国家等——结果被认为只是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此后,有关社会民主的一些讨论日益碎片化,往往专注于具体问题,而缺少有说服力的系统解释。这一特点在有关“美好社会”的讨论中也体现出来。如讨论中所提出的六个挑战(15)并没有什么新意,也未能产生将它们连接为一体的逻辑框架。如一些总结报告所强调的:“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因此缺乏一个清晰的纲领性政策导向。”(16)
欧洲激进左翼和其他力量的理论解释就更为多样化和碎片化了。如在欧盟问题上,许多反新自由主义、反欧盟的左翼理论解释或者如一些极左力量一样,把欧盟视为一个超越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17)或者如大多数欧洲左翼,依然在用传统的民族国家逻辑来看待欧盟。近年来,一些欧洲进步主义学者在反思左翼的欧洲立场后,认为欧洲左翼缺少替代性的纲领设想,同时强调:“从现在开始,欧洲左翼必须开始考虑如何超越欧洲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的‘错误必要性’(false necessity)。为此就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欧洲方式,后者限制了其选择范围。”(18)
四 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贻误
欧洲危机的日趋复杂以及相关政治力量的态度变化表明,在欧洲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欧洲政治渗透的影响要比人们最初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深远。从既已显示出的欧洲社会政治危机中可以看出,欧洲要走出目前的危机急需清理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政治贻误。
首先,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社会失衡。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演进表明,欧洲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模式的危机导致了客观的市场改革的需要,新自由主义本是作为应对欧洲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危机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方式而被人们、尤其是被主流政党所运用的。它因此拥有了一种政治合理性。但当这种合理性通过单方面的制度化方式渗透在国家和欧盟的制度结构中时,它转而行使了社会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功能,并渗入人们的灵魂,成为教育和经验判断的主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理性就不仅仅限于甚至并不主要集中于经济,它将市场价值观扩及和散布到了所有的制度和社会行为中。(19)
因此,新自由主义由一种市场改革的工具或政策手段演变成了一种市场政治逻辑。这种逻辑一经确立,新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即被放大了。注重资本的社会职能,注重国家对进步社会目标的促进职能和作用,注重和谐平衡的劳动关系,这些本是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和政策方式,都是以否定这些“成功”经验的要素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所突出的竞争虽加强了资本甚至国家的竞争能力,但却是以扭曲社会的平衡为代价的。本来,这种扭曲需要通过约束市场的制度规范或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性因素予以矫正,可一旦将新自由主义衍生为一种政治逻辑,尤其是当新自由主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嵌入在了既有的制度体系后,这种机制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削弱传统的社会体制,并进一步扭曲这种关系。欧洲危机中的紧缩政策突出显示了主流政党的这种困境。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的社会失衡是引发欧洲目前政治和社会危机的主要政治原因。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又使得欧洲更难以清理其贻误。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侵蚀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功能。在一些主流意识看来,民粹主义是目前欧洲民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其实,民粹主义的泛滥只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所导致的政治恶果之一。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政治逻辑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对民主多元选择的否定趋势。当新自由主义成为政治家用于应对危机和社会冲突的唯一语言,当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入国家以及欧盟的决策机制中,主流政党才失去了选择,民主也才失去了意义,民众也才有了对既有秩序的失望乃至寻求新的带有颠覆性的替代力量和政治议程的渴望。这些从本源上都可追溯至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政治寓意。一些进步主义的分析指出,在当代社会,对自由生存最大的威胁在于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中内含的人类的无情的工具化。当所有的事务都从属于市场的逻辑时,市场观就成了人类的唯一价值观,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货币来理解。声称没有市场之外的其他选择,实际上就是认为民主是无意义的,因为民主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有不同的替代选择。自由意志就是无效的了,因为除了市场的辩护者所称的国家政体的理想结果外,就没有其他的自由意志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的结果是市场极权主义。它展示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最终胜利。所有的人类生活和实践(上层建筑)被简化为一种经济基础。(20)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导致一些传统的左翼力量实际上失去了本应有的政治塑造能力。
民粹主义影响的扩大凸显了欧洲主流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在危机背景下在取舍政治立场和政策方面的尴尬态度。因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垄断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其他话语的缺失驱使民众涌向支持民粹主义的队伍。由于民粹主义对既有的政治秩序、尤其是主流政党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它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主流政党共同应对挑战,并捍卫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意志,但当既有的政治秩序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一种制度化时,主流政党乃至精英社会所捍卫的不过是一种市场极权主义。
再次,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极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上述政治影响相应的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欧洲社会关系的重新极化。探讨新自由主义强劲的生命力以及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追随,不能仅从制度层面寻找答案,还需要从社会关系中去说明。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并不只是国家是否“干预”的问题,而是财富和权力是建立和巩固在社会的一小部分人群手中的问题。由于缺少显著的社会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相同的利益集团依然拥有显著的政治权力去促进其利益并使其制度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就是,新自由主义继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挑战作为新自由主义计划基础的阶级关系的努力的可持续性和无效。(21)
由此人们也应该进一步思考一个曾经作为战后资本主义成功经验的命题,即阶级冲突的制度化。按照其解释,当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的一条准则得到认可,因此也得到了控制后,阶级冲突也就得到了控制。但这种制度化有一个前提,即它始于承认相互斗争的两派(即资方和劳方)都是合法的利益集团。劳动关系中的公民权利使得企业家和工人都能够联合起来并集体捍卫他们的利益。(22)应该说,这是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在处理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成功经验。可目前的问题是,虽然形式上这些合法的利益集团(包括工会)依然存在并拥有其形式上的权力,可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下,这种制度还能够起到其形式上的保护作用吗?这恐怕正是目前许多民众明知民粹主义的狭隘而宁愿接受它的原因。
重塑欧洲政治秩序不仅需要有制度上的平衡和选择,更需要有社会运动的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的平衡机制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证,更需要有一种社会关系的保证。后者主要指作为社会主要阶级之间的一种相对平衡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指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仅仅只靠所谓的“制度”保证,更需要有能够约束制度的社会运动基础。新自由主义政治首先打击的恰恰是作为资本对立方的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欧洲也不例外。只不过,撒切尔政府是以一种强制剥夺工会权力的方式来实现,而欧洲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逻辑下通过和平的方式(某种制度化的方式),逐步削弱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基础。社会需要一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权的前提下,有效的社会平衡必须要有抑制资本权力的制度空间和社会运动空间。
五 结语
欧洲危机的变化形势凸显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对欧洲的渗透及其对欧洲政治生态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危机之初,新自由主义在欧洲被一致声讨。可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变化,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如人们所预言的死亡,反而在以新的制度化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于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渗透,欧洲主流政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面对欧洲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欧洲主流社会在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民粹主义的挑战时,依然不愿触及新自由主义政治这一更深层的问题。但欧洲欲走出危机,矫正失衡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上清除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Paul Kubicek,European Politics,Longman,2012,p.298.
②Christian Marazzi,"Neoliberalism Is Destroying Europe",The Guardian,14 September 2010,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sep/14/neoliberal-europe-union-austerity-crisis,last accessed on 26 November 2016.
③Stefano Bartolini,"Political Parties,Ideology and Populism in the Post-Crisis Europe",Poros Conference,7-10 July 2011.
④卡斯·穆德将民粹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把社会从根本上分裂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普遍意愿的表达。”See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9,No.4,2004,p.543.
⑤按照西方主流意识的一般理解,民粹主义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政治方式,它主要诉诸那些感到自己被富人和拥有权力者剥削和压制的人们的一种偏见和感情。See Kenneth Newton and Jan W.Van Deth,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Democracies of the Modern World(Seco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07.
⑥所谓“民主的政治文化”,指支持普遍的民主价值观的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宽容、人们对其他公民的信任以及积极的社会资本。See Paul Kubicek,European Politics,Longman,2012,p.240.而这些恰恰是民粹主义有意摧毁的东西,也因此主流社会对之有所忌惮。
⑦Matthijs Rooduijn,"The Nucleus of Populism: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49,No.4,2014,pp.572-598.
⑧Stephanie Lee Mudge,"The State of the Art:What Is Neo-liberalism?",Socio-Economic Review,No.6,2008,pp.703-731.
⑨Michael Cronin,"Crossing the Elbe or Why we Need a New Culture of Dissidence",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7,No.2,2013,pp.136-148.
⑩J.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1982,p.392; Bojan Bugaric,"Europe Against the Left? On Legal Limits to Progressive Politics",LEQS Paper,No.61,2013,http://www.lse.ac.uk/europeanInstitute/LEQS%20Discussion%20Paper%20Series/LEQSPaper61.pdf,last accessed on 20 November 2016.
(11)Bojan Bugaric,"Europe Against the Left? On Legal Limits to Progressive Politics".
(12)Andy Storey,"The Ambiguity of Resistance:Opposition to Neoliberalism in Europe",Capital & Class,Vol.32.No.3.2008.DD.55-85,http://cnc.sagepub.com/content/32/3/55.short,last accessed on 24 November 2016.
(13)Andy Storey,"The Ambiguity of Resistance:Opposition to Neoliberalism in Europe".
(14)Andy Storey,"The Ambiguity of Resistance:Opposition to Neoliberalism in Europe",pp.55-85.
(15)即欧洲与全球化、不平等、可持续性、改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以及民主和政党的组织。参见Henning Meyer and Karl-Heinz Spiegel,"What Next for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The Good Society Debate and Beyond",Renewal,Vol.18,No.1/2,2010。
(16)[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夏庆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17)Sráid Marx,"The Left against Europe 4",https://irishmarxism.net/2014/10/18/the-1et-against-europe-4/,last accessed on 24 November 2016.
(18)Bojan Bugaric,"Europe Against the Left? On Legal Limits to Progressive Politics".
(19)Wendy Brown,Edgework: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39-40.
(20)Michael Cronin,"Crossing the Elbe or Why We Need a New Culture of Dissidence",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7,No.2,2013,pp.136-148.
(21)"Contesting Capitalism in the Light of the Crisis: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Harvey",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No.71,2012,pp.5-25.
(22)[德]拉尔夫·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参见[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王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