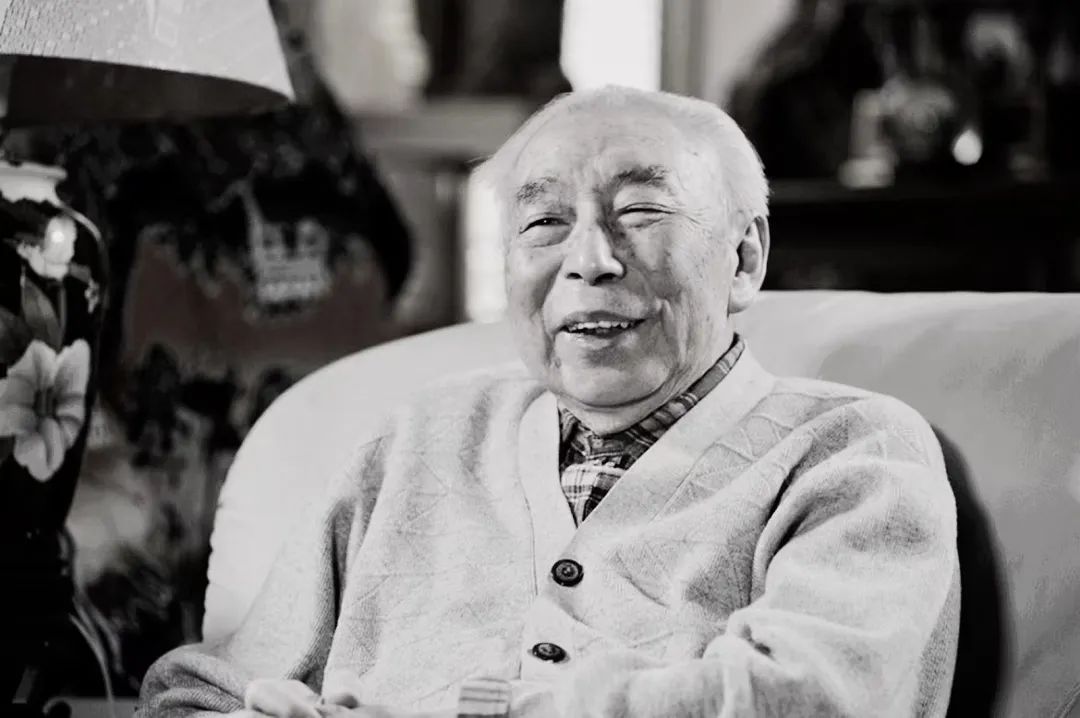牛旭斌:“一岁三行”寓同谷
公元759年的同谷,迎来又送走了一个人。他投靠同谷,最终却为过客。
这个人是杜甫,他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流寓陇右后,自秦州赴同谷,寓居月余。这是他弃官成布衣,为逃乱前往的唐之边境。他出秦州自礼县盐官经汉源石峡入龙门镇,携妇将雏所走的山道,与今天的十天高速走向同行一辙。然那时的一周一旬,驾撵的破车,现在开上汽车,不过两小时。
他之所以来同谷,是受佳主人邀请,那热情洋溢的长信,同谷粟亭的物阜丰裕,让他燃起生活的希望。他像耶稣进耶路撒冷时骑着驴驹到同谷,他想的是,待洛阳与长安战火若休国家安定后,就能速速回去,这地域虽偏,但亦远亦近。
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前,杜甫从立秋日启程,自华州始发秦州,白露节在秦州城,10月末往南奔,听说同谷竹复冬笋,崖蜜易求,薯蓣遍地,是无食时想去投奔的乐土,无衣时渴念养活人的南州。在同谷四十多天后,他于12月1日又自凤凰村出发告别同谷,到12月21日,辗转到达成都,这是他区别与以往平生壮游的行旅,准确说是谋生,是颠沛流离。
他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都是因为那方水土有熟人或有诗友。康震讲:杜甫每去一个地方,他会提前写信。他希望受到邀请,接到邀约,他方才安排行程。一介书生,总要在朋友面前,极力保留尊严。
此前在秦州让杜甫吃饱的是橡实与薤白,不论是东柯谷还是南郭寺,地近西北,同谷人叫作小蒜的薤白马上就枯苗了,遍野的草药也快枯萎。每天捡食橡实的日子,让侄儿杜佐感到难看,让家人受罪。穷愁绝境往何处?他心无明向。
秦州城里处处是抓兵役的儿逃母哭,安营扎寨的旗里,有吐蕃的颜色。还是走吧。一路上,和谁同程,半路上,丢了谁,他都没有说那么具体,不细记载,但自秦州至同谷至成都,他却如实记录了路线、起至与地名,以及沿线的风物、地理与见闻。
对秦州与同谷,他是在“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的不安中,被陇右的灵秀所打动了的,或者说,没有哪个阶段,他这样浓墨重笔地描绘过旅程风光。
“石门雪云隘,古镇峰峦集”,他已经打算放下奉儒守官的浩然理想,要在这群山绵延峰峦如聚的地方,与自然为邻了。这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能清晰又确凿地载明线路的,要数这段经历。他记下虎熊猿鹿的哀鸣与悲声,记下沮洳栈道湿细泉兼轻冰和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的山阻与道长。
这龙门东往同谷以北三十里的一座大山,叫泥功山,常年烟遮雾罩,泥翻淖深,杜甫当年从沙坝石龛走来,就翻过积雪盐白的草山荒岭,写下《泥功山》一诗:“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闻一多在对杜甫陇右生活的研究认为:“杜甫在秦州置草堂,卜居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投靠侄儿的杜甫在不到三月的秦州生活中,常常登上远地,目睹兵锋相戈。他说服自己不能再给亲友添乱了,他告诉杜佐:“我们要走了,我收到了同谷佳主人的信”。杜佐挽留,他还是决意再往偏远的南地走。他怕搅扰他们,怕他们劝阻他,他半夜起身。
其实,在杜甫心里,离开秦州前往“南州”同谷,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发秦州》的所言里:“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半生游。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谿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
他离开秦州时还称自己“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他似乎又是想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用亲友照顾打理的拘束,可能还会写出超过《秦州杂诗》的诗。
天下寒士,安得广厦?生事不谋,这是天下读书人的通病:生活料理能力差,懒于人际关系,不逢迎、笨拙、老实,荒于生计、疏于日常,不操持家务,不顾柴米油盐,不会关心人还会连累人,苦在心里,自己过不好却还忧国忧民。
我读过雪潇先生对杜甫在陇右的研究:“杜甫离开秦州后,真的想在同谷多住一些时间,他也真的不想,至少是那么快地离开陇右去四川。”
在同谷,他举家六人,搭茅茨于飞龙峡住了下来,吐蕃之乱下,他找不到约他的“佳主人”,空有一轮明月挂在万丈潭上空,也挂在蜿蜒峡谷的河里。
“佳主人”的爽约,不是逃避,或许是人无音信,但却无意给了同谷说不清的尴尬,甚至背上了不道义的黑锅,以致于千年过后,同谷还在为此自责。寓居同谷后,此前听说富庶的盆地,同样没有像样的能救命的衣食。他穿不能掩胫的短衣,日随狙公,挖黄独为食,夜访儒生,观凤台生忧。在凤凰山到大云寺连片的橡林里,他遇到了许多给他橡粟与黄独的同谷人,他们不相认识,但同谷人望着他带的小儿,都悄悄抹眼泪。
安史之乱与吐蕃东侵频繁的战火,让繁华的同谷大地,停止了欣欣向荣。活着的同谷人,并没有口粮可给他。翻山越岭拾柴禾挖草根的劳作中,他认识了很多与他踏雪挥锄、朝夕相伴觅食的同谷父老。一位养猴的老人带他进山,铲雪,挖药,他有时候空手而归,饿得孩子嗷嗷啼哭,山鸦哇哇惨叫,直到他作出不得不离开同谷的决定之际。
他想:大雪过后,春天就来了,雨恰好从天上赶到人间,汇入这奔走了日日又夜夜的青泥河水。星垂峡谷的夜色中,他在月下为驴添完夜草,返回茅屋坐在狂风四起的窗前,提笔写下寓居同谷县的《七歌》时,一种内心的挣扎与哀鸣,从洛阳到华州,又从华州到秦州,再从秦州到同谷,穿越颠沛流浪的风和雨,飞过阴沉的大地和天空。
在《发同谷县》中,他写下“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这是他不愿离同谷而去的心声,不愿再颠沛下去的心声。
他不是陶渊明,也不像苏东坡,身为杜审言之孙,无法放旷的知识分子,惨到何时,心里都还念着致君尧舜上的未酬抱负。他不忍遽去,然临歧别子,握手滴泪。
回望公元759年冬天的同谷,大河冻冰,寒峡奏风,确实有点不像陇右粮仓,五谷谦收,死鹿哀猿,让“舍书”好客的同谷,冷漠了不该“冷落”的诗人。
杜甫将身心僻隐同谷,却时刻梦回长安。在卿相已经多少年的当朝,他已白头蓬发,瘦骨长须,三年饥走荒山道,未及天命,却已身老。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写到:“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这在他写于陇右的117首存诗里,与同谷有关的诗,可以说道尽世情沧桑。
河流发源于深林,长歌发乎于心灵。此时此刻,他的心如穿峡的风那般呼啸。他掩了掩茅草,压住麻纸,蘸滤笔墨,惟有长歌可当哭,没有比这更为困顿窘迫的生活了吧,没有比自己更加悲伤困顿的身世了吧,他想了想国家朝纲,又想了想过往杂事,愁苦与凄楚如烟云,漫盖了峡谷与草屋。他声称自己做客同谷,做客,作客?客未做成,子美和妻子、弟弟杜占及儿子,都成了同谷的子民。天寒日暮,手脚冻皴,朝拾橡栗,雪铲草苗,常常空手而归。
同谷的冬天云雾晦冥,流落到这种地步,杜甫油然想念生别辗转、十年不见的三个弟弟杜颖、杜观、杜丰和嫁到安徽的妹妹,兵荒马乱之下一定活得不好?“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回到他们身边怕是无望了。同谷的“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把他的灵魂涤荡得干干净净,他说:“回故乡的路,此生已断了,而今只剩皮囊,孤魂已经还乡了”。
在《其七》中他还记述:“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长路漫漫,“停碜龙潭云,回首白崖石”,“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他近乎达到了绝望,孤独,失眠。同谷把他怎么了?仰视皇天,悄然终曲!人生半百,无可奈何!当他写完这七首诗的时候,他终止了所有的心潮澎湃,如释重负,悲也罢苦也罢,隐也罢逸也罢,生也罢死也罢,凤凰都是浮云,他搁笔望天,只见一轮白日在飞速地奔跑。
在同谷,他用心绝唱了这曲沉郁顿挫的歌,泪水交织的歌。无疑是生活上的一筹莫展,心灵上的无可依归,才让这“呜咽悱恻,如闻哀弦”的七歌,回彻在空广而苍凉的同谷旷野,从而让这段低光的时刻与哑然的故事,得到后世如今在研究杜甫上不可替代的价值推崇。
许多学者说:要想真正理解杜甫,要想领略杜诗何以沉郁何以顿挫,同谷是绕不过去的一段路。
也许你走过天下所有的草堂,但你不到成县的杜甫草堂,你说崇拜杜甫,我觉得你的了解是不够的,也是没有人相信。
《同谷七歌》可以说悲到了家,他悲的不是同谷,哀的亦不是自己,他歌的不是发生于同谷的那年那事,呼的也不是家眷情长。他说万丈潭里伏藏有龙,蝮蛇泳在其中,浦起龙认为此龙暗指皇帝,蝮蛇喻指安禄山、史思明,这是他的痛陈与控诉,更是他在同谷深冬里被风刮起的内心的呼号,兮字叠起,一咏七叹,交底说出“心里话”,说出来后,他连拽了几下裤腿,又带着木柄长镵,踏着积深的山雪去找挖黄独,山上传唱着《陇头歌》,他也跟着唱起来。
写完《七歌》之后的几天,他坐在凤凰村草屋,他攀上凤凰山南麓,他静听万丈潭,抬望秀才峰,他的心豁然比峡口还敞亮,比八十里同谷大川的脱缰平展还豁朗。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他自始至终是爱同谷的,并没有嫌弃同谷是一片穷谷。
贫穷并不拒绝表达,饥饿并不丧失追求,除了家人,他还有李衔、狙公、山寺僧人,有挖药为食的良友,他在诗中道出过这些情分。
深夜,重读他写在同谷的13首诗,于我,字字都如刻刀,字字又是伤痕,字字是风雪,字字是药食,又字字是林翮,字字是凤凰……
是字与字、诗与诗的反刍中穿越的仰望,是一字一顿一回首。
再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他说:“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成就。”杜甫的《三吏》、《三别》家喻户晓,但能知道陇右诗的却不多,知道杜甫来陇右来同谷的更是甚少。
有多少人追寻杜甫的脚步呢?他心里有凤凰和元气,他的影响跨越时空成为中国文人“五君子”之一,他是影响当代又将影响千年后世的曾在同谷山峡中瑟瑟寒颤的人。从此,天下诗人无不想到同谷一探究竟,来采撷诗圣贫贱不移超拔群伦的正气。如果能唤来凤凰,他宁愿一人承担苦难,用一己的心血为食。
赵鸿任成州知州时,最早意识到同谷对诗人的愧待。他发起了对杜甫同谷诗的刊刻,并到同谷草堂隆重纪念。他在《杜甫同谷茅茨》诗中写到:“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宋代之后,杜甫在文士心中更受推崇。北宋宣和年间,山东巨野人晁说之来任成州,曾作《濯凤轩记》《发兴阁记》《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三文,表达对杜甫的忠义崇敬之情。
《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现重刻后立于成县杜甫草堂牌坊后,《记》作于宣和五年五月,记文载:顾惟老儒士身屯丧乱,羁旅流寓,呻吟饥寒之馀,数百年之后,即其故庐而祠焉,如吾同谷之于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唯知其为人世济忠义,遭时艰难,所感者益深,则真识其诗之所以尊,而宜夫数百年之后,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虚徐,溪月之澄霁,则尚曰公之故庐,今公在是也。去年今日,有幸陪徐兆寿先生访草堂,读此碑,他认为杜甫来到同谷时同谷已遭吐蕃战乱或所据,耽搁了“佳主人”的声名。
同谷能有北宋时期的祠,可谓“神州第一祠”,这说明同谷人的厚道贤良,历代人崇仰杜甫,同谷的后世一刻也没有停歇对杜甫的追望与补憾。
再次说明同谷不仅长养庄稼,还长养文心。为了纪念杜甫在同谷漂泊的低光时刻,特立祠祀之,让去过成都草堂的人,溯游成县来追拜诗圣。
僻地成县,因此而在历史的册页中,显得格外厚重。
明代官员文士拜谒吟咏题咏成县杜甫草堂的诗作尚有多首,都是对《同谷七歌》等诗篇以及对杜甫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感慨,而以诗为记的粉丝读后感。再到后来,清人咏成县杜甫草堂的诗作有宋琬《杜子美草堂二首》、吴山涛《少陵草堂》、蒋熏《少陵祠》、杨注《少陵祠二首》、钟秀《少陵祠》、黄泳《成邑八景》等。这其中,八百年后追到成县的宋琬是一个最狂热的杜粉,他的《杜子美草堂二首》其二这样写:“少陵栖隐地,古屋锁莓苔。峭壁星辰上,惊涛风雨来。岁华三峡暮,身世七歌哀。欲作招魂赋,临流首重回。”斯人已逝,气若长虹,八百年过,灿若星辰。杜甫的峭壁,就是宋琬的峭壁,杜甫的惊涛,就是宋琬的惊涛,七歌哀罢,三峡岁暮,人生的遭遇,谁又不是如此?
凤凰山巍巍,青泥河汤汤。坐于万丈潭的石头上,看郊游的人群下河来也坐在石头上。青灰色的巨石横卧在河床,水流自谷底潺涓。
杜甫草堂起伏又蜿蜒的红墙里,因了杜甫的短暂寓居和写给身边的《凤凰台》《万丈潭》《同谷七歌》,而让飞龙峡及草堂、万丈潭及凤凰台名气飞扬,他在同谷居住行旅留下的多处遗迹,特别是他的诗作,把同谷的山水在千年之后,推给天下文雅之士和世人后学来拜祠问艺。
“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是这般无人之境,才有寻幽访胜、兴发逸兴的所在。他把同谷山水最早写入景中,成就了今天人们心驰神往的游览胜迹。
一个母亲对女儿说:“去磕个头吧,求点灵气”。杜甫青襟肃坐,清清瘦瘦的身躯手握书卷,而发生在759年不为人知的故事,藏在这尊泥塑诗人的心地,一种神圣的灵气,自峡谷浸洇着每个拜访者的胸膛。只可惜,野生的海棠和梅花并不一定知道,雨里下着杜甫的诗,他的精魂游荡在同谷衰枯过后又碧绿的山河里。
不想走,又不得不离开,你莫走,又不得不去求生。这个从小就漫游齐鲁吴越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壮志的人,此时俨然已放下顶戴虚荣与抱负,成为讨光阴写诗歌的流浪人。他听懂并学会了说同谷方言,尽管他做梦仍想重返长安“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但他在此收心了。一身布衣的人,就连梦打碎的声音,也不会有一点点响动。相反,有奔流的河声在穿峡的风声中,朝朝夕夕,一淙一涓淌过他的心。
月黑风高,他想念在远方的弟弟和在钟离的妹妹。呜呼七歌兮悄终曲,死悄悄的人生比飞龙峡还死寂一片。两条大河手挽着手,顺河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切不可能了,继续南下,就越走越远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吧。
那年他离开秦州时,中宵月半,有阮昉等朋友风雪相送;而离开同谷时,欷歔声里,也有李衔等“数子”来和他执手握别。
“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在同谷的李衔,还有狙公、邻舍和乡亲,他们把他送到了分路口,他握手,作揖,同谷人洒泪而别,目送他们渐行渐远,渐渐消失成风雪中的一团黑点。送行的人群,刹时如呜咽的河水。
李衔何人?杜甫晚年律诗《长沙送李十一衔》中写到“与子避地西康州”,这即是《凤凰台》中北对的西康州。李衔与杜甫相见于长沙的时间为公元770年,距离公元759年,恰好十二个年头,所以杜甫说:“洞庭相逢十二秋。”李衔,排行十一,曾与杜甫义结鸿儒,情同道友,曾一起寓居同谷(今甘肃成县),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中的儒生。
我们终于知道了在兵荒马乱吐蕃争战的同谷,杜甫还有同道中人。他在《积草岭》中写“食厥不愿余。茅茨眼中见。”他选择来同谷的主要根源,是来拜访与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已经穷愁潦倒的诗人,他尽管饿着肚子,食着厥薇,住着茅茨,胸中还有许多不甘的追求与理想,要与懂他的人说。他休驾投诸彦,幻想着见面的情景,幻想着佳主人来信中对同谷物产丰富的描述,仿佛已经面面相觑,秉烛夜谈。至于吃什么饭住什么地,他其实不在乎。
他“悲风为我从天来”的伤愁中,李衔是他的第一读者,他最早将子美与李白齐称,算是那个乱世岁月里最铁的粉丝。
好在杜甫自同谷下剑南到了成都,先后有严武、高适的帮衬,让他困苦的生活终算有了眉目,他结束漂泊,过上了为期十年较为平静的蜀中日子,受的罪比陇右少了,但回长安的梦想让他终生都徘徊在“竟非吾土倦登楼”的离忧中。
生为成县人,我四季去草堂拜谒,性情被濡染和颐养,每次都有激荡于心的感怀;随着年岁增长和对诗人心肠的理解,每次鞠躬磕头时的俯首屈膝,我一次比一次弯沉得更低。
冬月是平常的季节!是奈何的伤离!那一间依坡而建的茅屋,因为心怀致君尧舜的抱负,因为“我能剖心出”的诗篇而千秋流传。
阳光洒满凤凰台,投照碑廊,诗魂越过雄伟的殿宇,在字字句句的石刻上飘荡。
时间像旋风一样,又到了一年的十二月一日,又恰好是杜甫离开同谷的日子。带着每每读起《同谷七歌》的感伤,我抱着愧疚想:生活窘迫的诗人那份不变的爱民情怀,何悲?何苦?是因为他身陷失落的不失刚正,因为他置身草野的固守端直。我用一个同谷人的笔写这些,算是手捧黄独对诗魂祈祷!
(作者简介:牛旭斌,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散文作品见于《文学报》《人民日报》《散文选刊》《延安文学》《雪莲》《牡丹》等。入选《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1》《2018中国微信诗歌年鉴》《乡愁若灯》《2019中国精短散文年选》等30多个文学选本。著有散文集《风起离乡》《山河素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