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礼乐中华与道德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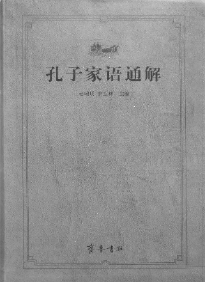
杨朝明部分学术著作
古代的冠礼与“成人”
了解儒家人学的实质,把握儒家关于“成人”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是早期中国的大智慧。关于这一思想渊源,不仅有理论阐发,也有具体的礼仪载体,这就是作为古代成人礼的冠礼和笄礼。孔子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西周时已经有系统的教育体制。一般而言,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左右,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人。行冠礼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成年”的认可,是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传统的冠礼,核心内容是三加冠,分别表达男子成人之义,寓意要“弃而幼志,顺尔成德”。人既然已经长大,就要摆脱孩子气,把成人德性固定下来,充实起来,就应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人而成人,就应当认同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表示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就不应像长不大的巨婴,不能使个人的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
冠礼是人生的基本礼仪,人成为“人”,就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要懂礼义,成人之后应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不管不顾。
《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社会基本关系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明白做人的基本要求。人行冠礼后,便应认同人伦,实践人义。
按照礼的规定,士人行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等尊长,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相应教导,这对于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国语·晋语六》说:“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刚刚成年的人要谨慎戒惧。进入成人阶段贵在开始,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加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可以遮挡风雨,只是需要随时清扫。人有正确目标,也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孔子常说到“仁”,在孔子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既成人,就应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有“仁”心,脱离人的纯自然状态,应该像“亲亲”“事亲”那样自然而然。
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
成人,是“人”的类存在的意义,是对人的普遍要求。然而,人组成社会,形成社会组织,就需要社会的管理者。中国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大人之学”,要所造就的“大人”有境界、格局大。
孔子儒家特别强调“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所看重的正是为政者的高品质与高素养。现实社会需要有人引领,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有一批明是非、知荣辱、有格局、能担当的君子、大人。“学以成人”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则是“学以成德”“学成大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人格养成的目标、政治品格的境界、为人处世的风范。“君子”是社会引领者﹑示范者﹐有时它就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该是高尚的人。孔子有“君子之德风”“君子喻于义”等说法,又有“君子怀德”和“君子怀刑”之说,君子应该怀抱德性,有做人的标准。“刑”与“型”通﹐有榜样﹑法式、典范之意﹐指君子明理修身﹐循道而行。内心充盈饱满﹐胸怀坦荡宽广,做事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也就具备君子人格了。
孔子认为,人能敬其身,才能成其亲。什么是“成其亲”?孔子说:“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成其亲”就是成就他的父亲。“君子”是崇高的名称,是百姓送给的称号,叫作“君之子”,这就成就了他的父亲为君。在那个时代,君是德位相配人,有地位,有德行,受尊敬。君子是有教养的人。称一个人有教养,为“君子”,就间接夸赞了他的父母和家庭。
在孔子儒家语境中,“大人”“君子”是能够把握礼乐本源的人。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些圣王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尊,就在于他们思考深入,贴近百姓,知民之性,达民之情。礼的本质意义是什么?《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那么,怎样深层次把握礼?正如孔子论述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人立于天地之间,礼乐也本源于自然,扎根于生活,依顺于人情。就像战国竹书记载的大舜,他当年“旧(久)作小人,躬耕于历丘(山)”,故能理解礼乐的真谛、社会的本质、生活的真相。
人文学术在于化成天下。古代“大学之教”是关于穷理、正心的教育。儒学教人成大人,做君子,培养社会引领者。《大学》的“大学之道”,《学记》有具体阐述,其中论述教育要由经文入手,培养学生的志向、德行、品质、能力,最终使学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古代大学之教究心穷理,发奋立志,注重修道做人、从政治国,很有价值。它能把握道德教育规律,强调系统性,循序渐进,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今日人文教育之借鉴。
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人们越来越看到中华经典、中华礼仪的价值,期望在中华礼乐文明中汲取智慧。回望五千多年的文明,人们追寻并诠释什么是价值?什么有价值?何种价值优先?中华先人追寻人与天地,与亲人、朋友,与他人,与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价值定位,以安立社会和国家,安立个人当下与未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使人生、社会、国家变得更加美好,一定依赖心灵抉择与价值皈依。我们期望这一切,如果靠单纯模仿西方所谓“现代性”肯定不可企及。礼乐中华有极其丰厚的文化滋养,经由这里成就道德人生、高贵气质,应该是有志气中国人的共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