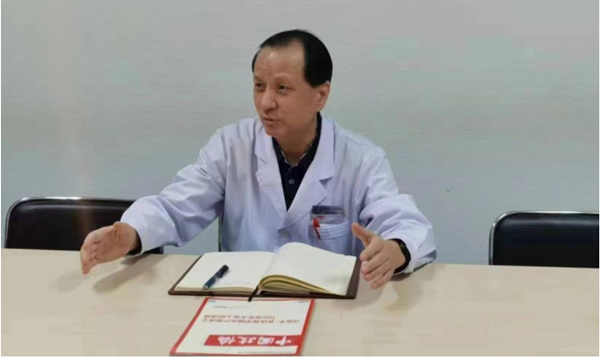学术交叉与精神互文
佛教研究在现代学术中,往往因执于实证主义一端而浮于能指的名相与符号。然而,这一平面化的学术旨趣从来都是与其反题——即通达佛教内在逻辑与精神价值的诉求——相伴相生,无论此种反题是出自学术体制的自反,是源于时代思潮,还是自发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佛教传统内部。本文立足这些交互交叉的线索,考察佛教与佛教学在中西学术语境下的形貌,并探索宗教学学科和“宗教中国化”双重视域下可能的佛教哲学研究范式。
佛教作为东方思想与知识传统的重要一支,长久以来作为镜像之物受到有同等知识诉求的西方学人的观照。近代佛教学研究的建立是西方思想脉络中理性和信仰这两大正统支柱在东方想象中的投射。欧洲古典佛学家遵循启蒙理性家法,以新教模式为组织和阐释原则,建立起由比较语言学而哲学阐释的佛教研究范式。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兴起与研究范式的转型,学院派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对经验维度的开放,即强调经验对于佛教义理书写的塑造作用。佛教哲学研究大家塞弗特·鲁埃格(David Seyfort Ruegg,1931—2021)1995年发表于《国际佛教学协会学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关于哲学在佛教研究中的地位的一些思考》(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一文,可谓是倡导这一方法论的典范之作。塞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佛教中,解脱学、灵知学和认知学往往紧密交织在一起,佛教思想(Buddhist thought)并不能如早前所认为的是逻辑实证主义或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哲学’”。这一同时内含经验维度的佛教哲学认知范式,引导我们更接近本质地看待佛教思想的内涵结构与成型过程。
中国现代佛教学建立于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背景。龚隽发表于2020年第1期《世界宗教研究》的《宗教史研究如何面对经验与文本:以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为例》一文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学研究“大都是在传统经学与近代新知交错复杂的融合中开展出来的”。接受了西方历史语文学规训的新史学家们,往往基于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观念化经为史,把佛教经典置于历史流变中把握。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后,中国佛教学不是“附丽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当中”,流于“心性论阐明”,就是在前者陷入范式僵化后重回“以较为精致的文本文献学与历史研究为主导的书写”。总之,“我们现代许多看似符合学科与学术制度规范的佛学创作,使传统经学系统瓦解的同时,也把宗教史论述中的道体与文本解读的存在性经验轻率地消解了”。面对这一困境,龚隽从民国时期佛学大家欧阳竟无“经验为宗、理性推度为辅”的内学研究中为当下佛教研究寻找到方法论启发:一方面“遵守新知(主要是历史语言学)的学术规训,同时又把这种新知严格限制在佛教事相的层面”,另一方面则“从佛教经学的内部来做思想的阐发”,即“保留住宗教经验”并将此内化于佛学解经中。
无论是塞氏的西学洞见还是欧阳氏的内学启发,都主张把学术从故纸堆的名相纠缠中解放出来,看到佛教这一学修并进的实践—知识体系中,义理表述与经验结构之间相互生成、相互形塑的辩证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典佛教研究唯历史语文学至上的文本主义态度。同时,佛教哲学研究对经验维度的开放,非但无害现代学术的实证性,反而能更接近真实地揭示出佛教知识与理论的生成逻辑,以及不同脉络的思想理路在与经验结构的互文中如何交织发展。另外,佛教义学流派层出不穷,尤其在多语种跨文化语境中更是展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实践导向的知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佛学叙述路径对学派/教派界限以及不同名相系统的依赖,进而还原出一幅更为清晰而深刻的佛教思想图景。
现代佛教哲学研究对经验维度的开放,与宗教现象学路径不谋而合。笼统来说,宗教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致力于从宗教经验的本性和结构出发探求宗教的本质。这一宗教学路径肇始于19、20世纪之交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时人们意识到实证主义态度对宗教研究的化约性影响,尝试从人类经验中所显现的宗教现象及其关联性出发进行探索。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及其所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可谓是宗教现象学研究路径的集大成者。尽管伊利亚德自我定位在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领域,他的研究取径却有赖于宗教现象学的理论支撑。伊利亚德基于宗教本质的不可化约性阐明“神圣”的现象学结构,并以此为理论出发点探索宗教现象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种种文化表现。其对佛教研究的启发在于:通过佛教文本与图像研究,从佛教经验现象的复杂表述和历史演变中,提炼出背后所蕴含的关于认识、阐释及更深层精神结构的内涵,并由此返回到具体时空语境,对不同的佛教表述加以比较分析。由此,对佛教的这一“宗教史学”研究在借助历史语文学、图像学等实证方法的同时,在阐释学关怀上保有宗教学的学科主体性。
宗教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有利于在佛教哲学研究中界定和激发更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并为思考、分析和表述提供恰当的概念工具。但我们仍需谨防落入“以西观东”的“反向格义”怪圈中。现代宗教学的概念语汇、范畴标准和预设前提,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西方学术对基督教传统的观察与研究。若不作辨析就贸然用这些概念和范畴去界定和诠释佛教于中国乃至亚洲之存在,许多有意义的佛教经验和理路就会被过滤,佛教本身的主体性叙述也就无从建立。我国佛教研究要突破这一困境,有赖于我们从中国佛教的本土表述和内在逻辑中发掘出理论意义。
“佛教表述”对于宗教学理论的一个可能贡献是,佛教文化可以从实践经验维度对宗教现象学进行有益补充。宗教现象学家擅长从表达终极体验的宗教语言中抽取出人类宗教经验普遍的现象学结构。佛教不仅拥有多语种、跨文化的丰富表述可资承载宗教现象学功能,更是提供了如何通达这一现象境界的实践路径。一个典型的“佛教现象学”例子是最早可见于《入楞伽经》的大乘无分别观修:先止息外境分别而内返住于唯心,再证得无二心识离主客二元对立,后超越此无二心识住于无分别智境界。这一次第观修进路作为共通的大乘修习目标,纵贯大乘经院哲学书写。中观、瑜伽行乃至二者综合等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学派,无论它们采取何种阐释模式与视角,均是对无分别观修所做的或本体论或知识论层面的合法化。这一观修模式在中国不同历史文化坐标中的种种表述及相互继承、挪用、误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或可为宗教现象学打开“中国化”的理论探讨。
上述大乘无分别观修建立在由粗至细、层层破立的次第进阶范式上,每一阶段认知境界超越且涵摄前一阶段,既体现了大乘佛教对世界终极本质的认识,也指明了在认知层面抵达这一终极的实践路径。这对于佛学之外的研究视域而言意义何在?我们看一下西方学术对“存在巨链”的发现和发明。
比较宗教学家普遍认同“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是前现代(主要是西方)各宗教和智慧传统的世界观核心。所谓“存在巨链”,即从物质到身心再到精神层面层叠交织的现实世界图景,每个较高层次超越且涵摄前一较低向度。观念史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1873—1962)在其《存在巨链》(1936)一书中旁征博引,论证这一世界图式在前现代西方各宗教传统中的普适性。他还从西方思想史对柏拉图的注疏传统出发,梳理了对立的两种柏拉图思想遗产,“一”策略和“多”策略——“一”强调万物本源,“多”强调造物多元。在洛夫乔伊看来,“一”和“多”在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体系里并不冲突,而是构成了完美的回环:在抵达本源的“一”后,仍返回拥抱“多”的创造性,“一”要在“多”中显现自身。由是,“存在巨链”就有了运动上的方向性,即从“多”到“一”的上行和从“一”到“多”的下行。完整的认知图式也不再是仅抵达孤立的彼岸(离“多”的“一”),而是此岸和彼岸统一于上行和下行的回环之中。
这一图式与大乘无分别观修恰好构成了某种东西方互文。《入楞伽经》各语种的流通版本和相关注疏传统,对无分别观修次第中代表终极境界的“大乘”或“极胜智”是否在“无相”中被见到有不同说法:若无相中“见大乘”,则究竟止于无相空性,为无相涅槃说;若“不见”,则须“无相”之上建立“有相”,以某种超越空性的实在为究竟,为有相涅槃说。“见”或“不见”,在义学层面历来是诤论不断的两条平行进路。而在经验层面,用大乘佛教名相表达就是:由色而空的无相涅槃是用“般若”看透万有幻相本质的上行路径;由空返色的有相涅槃是证得“大悲”幻化万有的下行路径,二者圆融无碍则是“不二”。“无相”即是由多到一,“有相”是由一返多,“不二”则是动态的回环。佛教知识传统对于比较宗教学乃至宗教学的理论贡献恰在于,为这一“存在巨链”图式提供多语种跨文化的义学阐述之外,还从认知/经验维度对其作出了丰富且有效的补充。
学术建设与时代需求:体认佛教于中国之存在
当然,这一宗教知识的东西互文并非是新鲜发现。尽管欧洲古典佛教学遵循启蒙所开实证家法,从语文和文本出发,把佛教知识构筑于理性上,西方知识界从经验维度对佛法所作的灵知学观照一点不晚于那些启蒙思想家。在理性知识与正教信仰之下,西方思想脉络亦含有第三条神秘灵知学思潮隐流,强调个体与存在本源发生内在勾连这一灵知(gnosis)开显过程。这一暗流作为每个时代主导结构的反题,不断试图冲破学院派与正教联合铸造的牢笼,为个体精神锤炼保留空间。佛教及其所代表的东方“灵知学”知识传统,成为19世纪以来几次神秘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精神源泉和知识参照。
张亚辉在评述张卜天译《西方神秘学指津》一书时指出:“当整个世界都除魔的时候,现代理性与科层制取代了城邦宗教和天主教会,在强迫每个个体都变得更加自由的同时,对灵魂的束缚却更加残酷和彻底,神秘学则提供了几乎同样自由的宗教超市,超市里可供选择、用来拯救自身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不菲。”在现代性裹挟下,佛教日益成为西方人宗教超市货架上可供选择的精神商品,抑或更严苛来说,成为宗教产品流水线上可供与其他知识自由组合的原料组件。
张亚辉也指出,“西方神秘学一个核心的特征在于,不论范围如何蔓延、系统如何庞杂,它总是能够和理性与宗教形成清晰的界限”,“而东方神秘学,亦如韦伯所言,总是无法清晰地区分知识与灵知”。诚然,这与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性格和政治社会组织方式息息相关;同时也启发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功能意义的实践系统整体,佛教不止于灵知部分,理性知识和信仰实践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也解释了佛教何以既能成为启蒙思想家以新教想象组织起来的研究客体,又能为神秘学关注者提供东方语境中的知识参照。而理性知识与超越性灵知在佛教系统中的统一,恰又是学院派佛教研究突破文本主义的桎梏、进而对经验维度开放的题中之义。
在中国,人文学术同样受到时代脉络和属于这个时代的知识范型(epistemes)所左右。到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庞杂的“宗教市场”。作为时代书写者,我们对佛教的学术观照又将如何积极参与到塑造和引领时代洪流中去?“宗教中国化”的时代要求下,前述以历史语文学为分析工具、以宗教现象学为逻辑枢轴的佛教学研究路径,或可在沟通东西方宗教认知的同时,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和恰当地体认佛教在中国这一丰富多元多样的历史文化坐标中之存在,进而更好发挥新时代宗教学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经验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阶段性成果)